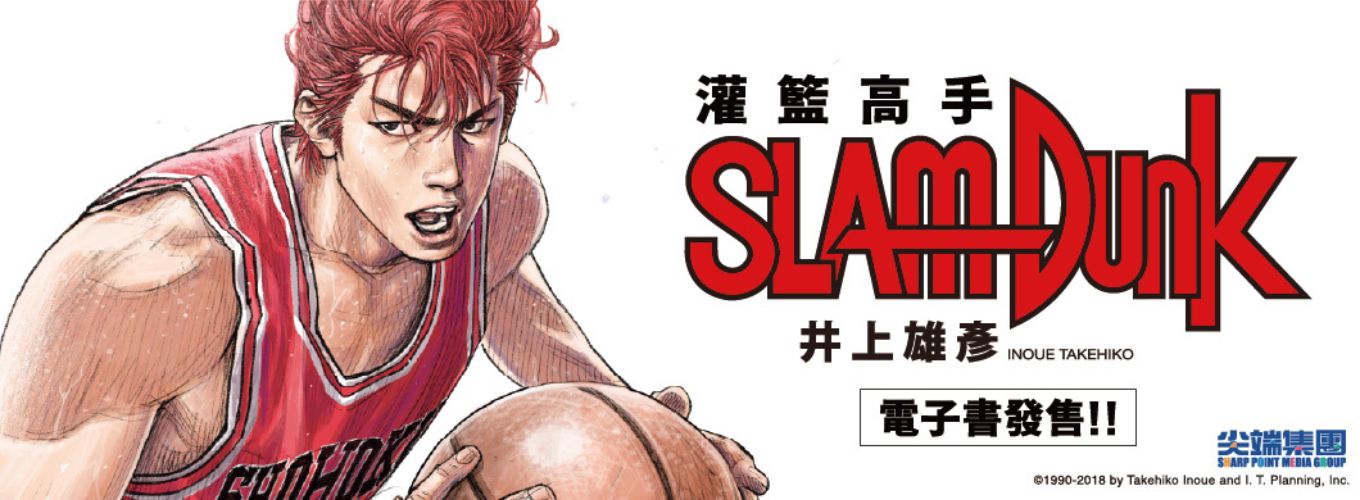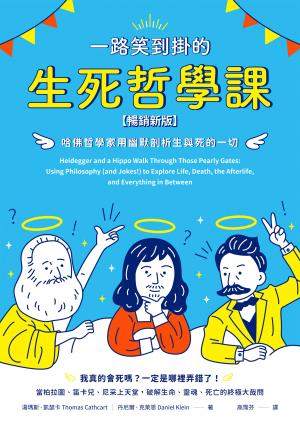呃,戴瑞,你還沒回答。你真的覺得自己會死嗎?
「是啊,當然。人皆難逃一死。法蘭克.辛納屈就死了。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死了。拿破崙、杜魯門、成吉思汗還有我老婆的愛德納阿姨也都死了。按照這個邏輯,有一天我也會死。我確定自己會死,就跟我確定蘋果是往下掉、不會往上跑一樣。」
戴瑞,你說得很好,但我們問這個問題不是要你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思考方法來回答眼見為憑的答案。我們要的是你「意識」中的答案,你在休息、放鬆時的意識的答案。那麼,現在,你真的相信自己的時日有限嗎?你真的相信逝去的每一刻都會從你活著的時間中被扣掉嗎?你真的相信人生到了盡頭時,自己所有形式的存在都會化為烏有?
……啥?戴瑞,說大聲點我聽不見。我們知道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大哉問,也許我們可以替你解答。
我們猜你內心最深處可能並不相信自己會死,因為你是個文明人。不用因此感到羞恥──至少還不用。人類有個大毛病,就是我們的意識很難接受、消化死亡這件事。所以我們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抗拒死亡的概念。實際上,我們所身處的文明世界的社會結構、習俗會推波助瀾,讓我們更傾向於抗拒死亡。
二十世紀的文化人類學者恩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在他的巨作《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中寫道,雖然客觀上我們知道人終必一死,但我們還是會想出各種伎倆來逃避這個能摧毀一切的真理(貝克爾的著作得了普立茲獎,但他在領獎前兩個月就過世了,走得最不是時候的應該就屬他了)。
人類抗拒死亡的原因其實很明顯:死亡這件事實在太可怕了!死亡是人類最終極的恐懼。這種恐懼會逼我們面對現實,意識到自己生而在世的時間非常短暫,一旦離世,就永遠回不來了。死亡的時鐘在耳邊大聲滴答作響,我們又該如何享受人生呢?
貝克爾認為,多數人用「幻覺」──「大幻覺」(the Big Delusion)來面對死亡。貝克爾表示,「大幻覺」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動機,比性慾還要基本。大幻覺進而造就了各種不同的「永生系統」,永生系統是非理性的信仰結構,使人相信自己可以長生不死。面對死亡,現在還有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策略,就是讓自己隸屬於某個可以延續至永恆的部落、種族或國家,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另外還有一派人用藝術來達到永生,藝術家預見自己的作品永久流傳於人世,如此一來,藝術家本人也隨其作品在大藝術家的萬神殿中留存了下來,或至少可以以簽名在一幅日落寫生畫上的形式,被保存在後代子孫閣樓角落。
最炙手可熱的永生系統,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中看到,例如東方信仰中,靈魂會作為宇宙能量的一部分繼續存在著,或是西方文化中,人死後與耶穌同在的世界。另外還有比較沒那麼崇高的「財富永生系統」。這個系統賦予我們每天早上起床的微小動力:上班掙錢。這樣我們就可以不去思考自己的大限。金錢也是人類進入權勢階級(另一個永存系統)的入場券。此外,這個系統還有一個附加好處:我們可以把自己的一小部分,也就是我們的錢財,留給下一代。
不過,買方自慎!(用白話文來說就是:投資一定有風險)
鮑勃得知重病的父親死後會留下一筆財產給他,便決定討個老婆一起享受這些錢,於是某天晚上,鮑勃來到了交誼酒吧,他在酒吧看到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
鮑勃深受這位容貌姣好的女子吸引。他走向女子,對她說:「雖然我只是個平凡人,但我父親再一、兩週就會過世了,屆時我可以得到兩千萬美金的遺產。」
女子深受感動,當天晚上就跟鮑勃回家。三天後,女子成了鮑勃的繼母。

「早知道我應該多買點廢物的!」
你可能會想,你發過「貧窮願」(或你是中產階級),所以此路不通,但貝克爾要你先別急著下定論。你在生活中可能還是有某些世俗的追求,讓你覺得自己可以永遠流傳於人世。舉例來說,你追求「潮」、「聖潔」,甚或是「自成一格」──這些都是一樣的。你仍舊是買了終極幻覺的帳,認為可以替自己微小脆弱的個體賦予更崇高的意義,藉此騙過死神,讓自己比生命更偉大……藉此戰勝死亡。
貝克爾說,只要你仍是文明人,這些幻覺就會持續下去。幾乎所有文明社會都會發展出一個普世的永生系統。實際上,這些系統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沒有這些系統,對死亡的不安絕對會使人類喪心病狂,文明也沒有辦法延續下去,我們將會回到原始的叢林時代。否認死亡是文明社會的生存法則!
同一文化中的其他成員若和你有相同看法,要維持這樣的幻覺便容易多了,若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的人也有相同看法,那就更好了。來看看卡拉和她丈夫共有的幻覺:
卡拉在醫院對心理醫師說:「醫生,你得幫幫我老公,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台冰箱!」醫生回:「沒事,無須太過擔心。很多人多少都會有些無害的幻覺,過去了就好了。」
「不是,醫生,你不懂,」卡拉很堅持:「他睡覺的時候嘴巴會張開,但我只要一點微弱的光源就會失眠。」
令人遺憾的是,永生系統卻也會使我們做出不理智的行為。當我們認定自己隸屬於某一個系統,也盡其所能投入其中時,就會開始排斥其他系統。世界各大宗教間的衝突屢見不鮮,也因此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可能每個永生系統都是合理的,而其他系統一定是錯的。
不過,文明也發展出了解決方案:殺光意見不同的混蛋!只要這些人死了,我們對永生的看法就不會受到威脅。嗯,感覺滿管用的。

寫這什麼鬼話!

「你選錯教了,就是這樣,我沒什麼好說的了。」
某天我在過橋的時候,看到一個男的站在橋上,準備跳下去。我跑過去對他說:「不!不要跳!」
「為什麼?」他說。
「世界上有很多值得你活下去的事情!」
「例如?」
「嗯……你有宗教信仰嗎?」
他說有。
我說:「我也是!你看,我倆有共通點!我們來聊聊!你是基督徒?佛教徒?」
「基督徒。」
「我也是!你是天主教還是新教?」
「新教。」
「我也是!那你是聖公會的還是浸信會的?」
「浸信會。」
「哇!我也是耶!那你是神教會還是主教會?」
「神教會!」
「我也是!那你是傳統神教會還是改宗神教會?」
「改宗神教會!」
「我也是!那你是一八七九年改宗的浸信神教會,還是一九一五年改宗的浸信神教會?」
他說:「一九一五年改宗的浸信神教會。」
我說:「去死吧!你這個可惡的異教敗類!」便把他推下橋了。
如果你很忙,菲利普斯還有一個精簡版:人一生中最難熬的,大概就是你不得不殺了自己最親愛的人,因為你覺得他是惡魔。
一個偉大哲學家的幻覺
是另一個偉大哲學家的智慧
貝克爾堅信,否認死亡是人類的大幻覺,而這種想法背後伴隨著一種「正統血脈」的心態。心理分析之父/潛意識學說之母佛洛依德在小論文〈幻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llusion)中提到,對死亡的恐懼促使人類創造並捍衛「神/宗教的幻覺」。因為人類在面對死亡時非常無助,所以我們的潛意識便自行創造出一個「天父」的角色,來幫助我們戰勝死亡。
佛洛伊德表示,這個天父角色也會獎賞善行,於是人類便有強烈的動機來抗衡各種反社會的天性,例如「亂倫、食人、嗜血」等。但最重要的是,這個終極的天父角色可以替人類減輕對死亡的恐懼,只要我們迎合社會的要求,祂就會賜予我們永遠的生命。
簡而言之,佛洛伊德認為「相信神」以及「相信神應許之永生」是用來幫助我們逃離死神的文化產物。
佛洛伊德從來不怕人非議,後來他也寫了《死亡驅力 》(Todestriebe,常被誤譯為《死亡本能》)。佛洛伊德原始的假說是:生存本能(愛慾,Eros)是生命、愛情、愉悅感、生產力的驅力,也是人類最原始的動機。但是隨著佛洛伊德年紀漸長,他開始看輕人性,發現這一切之中也有其他決定性因素存在著(還是不怎麼美好的因素),因為生存本能並沒有辦法解釋戰爭以及混亂。所以,我們要來討論死亡驅力。
從正面角度來探討死亡驅力,它代表人類需要脫離刺激,尋求和平、寧靜,有點像是死亡的彩排、預演。佛洛伊德稱此為「涅槃原則」(Nirvana principle),也就是一種「把生命中一切紛擾轉化成無機的恆定狀態」的需要。而我們自身也會去滿足這項需要;曾經坐在沙發躺椅上看保齡球比賽的人應該都懂。
所以我們應該用死亡趨力來克制自己,對嗎?佛洛伊德可不這麼認為。死亡驅力非常強大,一旦被放了出來,就如同猛獸出閘。保齡球比賽是無法滿足這隻猛獸的,牠不但是受虐狂、還有自殺傾向!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死亡驅力轉而對外,是嗎?不!佛洛伊德不認為。因為這樣的結局便是謀殺、混亂和戰爭。哎呀!那到底要我們怎麼辦呢?
佛洛伊德說,去看心理醫生吧。心理治療的終極目標、生活的終極目標,就是平衡死亡驅力和生存本能,並在這兩者之中找到平衡。
心理學家榮格怎麼說?
曾師承佛洛伊德的瑞士分析派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辯道,雖然神、宗教、永生等觀念源自於我們的潛意識,但並不代表這些概念沒有任何實際價值。
也許人類的潛意識比意識更有智慧、也許被佛洛伊德認定是由潛意識捏造出來的東西,其實是潛意識對事實的印證、也許宗教不是我們虛構的,而是我們從內心發掘出來的、潛意識中的心靈(psyche)也可能可以代代流傳,自行進化、越來越聰明,而我們的意識僅能望其項背。
榮格認為,宗教其實反映了人類的心靈,因為宗教是「內心深處」的符號。這些符號是人類潛意識深處的產物,所以有著強大的揭示力量。只有在睡夢中、各種神祕的文化以及宗教裡,這些符號才會出現在意識中。
當人類的意識無法接觸到心靈的深處、與心靈分離時,我們就會發展出一些神經質症狀,例如「終極的無意義」引發的重度憂鬱。

「聽著,我沒辦法讓你變快樂,不過我可以為你現在痛苦的原因提供一個十分吸引人的故事。」
靈魂出竅,真的可能嗎?
榮格若能再活久一點(他於一九六一年過世),可能就會開始借助迷幻藥來通往人類更深層、更高深的心靈層面。六〇年代,有很多人使用魔菇和迷幻劑來尋求超凡的頓悟,試圖了解(當時認為的)「更高的真實」(Higher Reality)。
不過就我們所知,藥物產生的這些感受都遠不及吉兒.泰勒(Jill Bolte Taylor)的親身經歷,泰勒曾在體外仔細觀察自己中風的過程,還歷歷在目、相當清楚。一九九六年,這位哈佛腦神經科學家在她左腦失能時見證了不可思議的景象。整個過程中,泰勒博士真切體驗了榮格所心心念念的「靈魂出竅」。
泰勒說人類的右腦負責處理當下所經歷的一切。右腦接受現在正在發生的視覺、聽覺和味覺刺激,用圖像思考法把這些訊息統整起來。在右腦中,我們是「完美、完整而美麗」的。我們認為自己是一種「能量存在」,和宇宙中所有的能量以及全人類的能量互相牽連。
另一方面,人類的左腦採取條理分明的線性思考。左腦會接受當下的刺激,找出其中的各種細節,將這些訊息和過去的學習經驗做連結,進而預測未來。左腦採語言思考而非圖像思考,告訴我們「我是」。在人類的左腦中,我們和周遭的能量流沒有關聯,和其他的人類也沒有關聯。泰勒中風的時候,左腦嚴重失能。
左腦失能時,泰勒開始感覺自己脫去了一切束縛,與宇宙中的所有能量合而為一。她感到平靜和狂喜。但同時,泰勒的左腦(大腦控管焦慮感的部分)還是會時不時地傳遞出「妳快死了!趕快尋求協助!」的訊息。但是在左腦無法完全正常運作的狀況下,要尋求協助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儘管她還是順利拿起電話找救兵,但當她想要解釋這一切的時候,卻只能發出狗吠聲。
後來在醫院的時候,泰勒覺得周遭非常吵雜、一片混亂,忽然又馬上感受到自己的靈魂在一片「狂喜之海」中浮了起來。
泰勒的結論是?她感覺世界上充滿了可以自由「移動到左腦右方」的人,這些人充滿了愛與和平。人類不僅僅是「推動宇宙的生命力」,同時也可以是和宇宙、他人完全無關的存在。最厲害的是,在某種程度上,人類有能力可以自行決定在哪個時間點要當哪一種存在… 閱讀完整內容
榮格若能再活久一點(他於一九六一年過世),可能就會開始借助迷幻藥來通往人類更深層、更高深的心靈層面。六〇年代,有很多人使用魔菇和迷幻劑來尋求超凡的頓悟,試圖了解(當時認為的)「更高的真實」(Higher Reality)。
不過就我們所知,藥物產生的這些感受都遠不及吉兒.泰勒(Jill Bolte Taylor)的親身經歷,泰勒曾在體外仔細觀察自己中風的過程,還歷歷在目、相當清楚。一九九六年,這位哈佛腦神經科學家在她左腦失能時見證了不可思議的景象。整個過程中,泰勒博士真切體驗了榮格所心心念念的「靈魂出竅」。
泰勒說人類的右腦負責處理當下所經歷的一切。右腦接受現在正在發生的視覺、聽覺和味覺刺激,用圖像思考法把這些訊息統整起來。在右腦中,我們是「完美、完整而美麗」的。我們認為自己是一種「能量存在」,和宇宙中所有的能量以及全人類的能量互相牽連。
另一方面,人類的左腦採取條理分明的線性思考。左腦會接受當下的刺激,找出其中的各種細節,將這些訊息和過去的學習經驗做連結,進而預測未來。左腦採語言思考而非圖像思考,告訴我們「我是」。在人類的左腦中,我們和周遭的能量流沒有關聯,和其他的人類也沒有關聯。泰勒中風的時候,左腦嚴重失能。
左腦失能時,泰勒開始感覺自己脫去了一切束縛,與宇宙中的所有能量合而為一。她感到平靜和狂喜。但同時,泰勒的左腦(大腦控管焦慮感的部分)還是會時不時地傳遞出「妳快死了!趕快尋求協助!」的訊息。但是在左腦無法完全正常運作的狀況下,要尋求協助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儘管她還是順利拿起電話找救兵,但當她想要解釋這一切的時候,卻只能發出狗吠聲。
後來在醫院的時候,泰勒覺得周遭非常吵雜、一片混亂,忽然又馬上感受到自己的靈魂在一片「狂喜之海」中浮了起來。
泰勒的結論是?她感覺世界上充滿了可以自由「移動到左腦右方」的人,這些人充滿了愛與和平。人類不僅僅是「推動宇宙的生命力」,同時也可以是和宇宙、他人完全無關的存在。最厲害的是,在某種程度上,人類有能力可以自行決定在哪個時間點要當哪一種存在…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