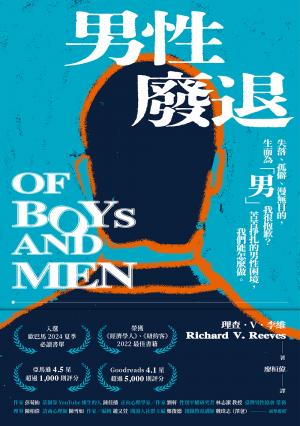第1章 女孩得第一 男孩學業落後
Boys Are Behind in Education
美國教育理事會前首席經濟學家卡羅.法蘭西斯(Carol Frances),形容它是「驚人的急遽上升」與「非凡的成功」1。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高級分析師史蒂芬.文森-蘭克林(Stephan Vincent-Lancrin),說它「很驚人……大家都不敢相信」2。
對於《男人末日》的作者漢納.羅森來說,它是「本世紀最奇特也最深刻的變化,尤其幾乎全世界都在以類似方式展開」3。
法蘭西斯、文森-蘭克林和羅森在講的,都是教育中的性別落差。才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女孩和女人的學業不只追上男孩和男人——她們已經輕鬆超越了。一九七二年,美國政府通過指標性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以促進高等教育的性別平等。當時,男性取得大學學位的比例比女性高了一三%4。到了一九八二年,這個落差已經消失。到了二○一九年,學士學位的性別落差是一五%,比一九七二年還大——只是這次是女高男低5。
男孩在課堂上表現不佳(尤其是黑人男孩和出身貧困者),嚴重傷害到他們在就業和向上經濟流動性方面的前景。根據目前趨勢,減少這種不平等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且許多趨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都惡化了。以美國為例,二○二○年大學註冊的人數,男學生下跌幅度比女學生大七倍6。男學生在線上學習方面也比較掙扎,而且過了幾個月、幾年,學習落後的程度變得更明顯之後,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男孩和男人的落後程度更為嚴重7。
第一個挑戰是說服政策制定者:在教育方面,現在是男孩處於劣勢。有些人辯稱,現在擔心這個教育方面的性別落差未免太早,因為薪資落差依然是男高女低。第二章我會討論更多薪資落差的議題;至於現在,不必多說,勞動市場的結構依然有利於不必照顧小孩的勞工,而且這些勞工多半是男性。但與此同時,教育體系的結構有利於女孩和女性,原因我會在本章說明。
所以說,我們的教育體系有利於女孩,但勞動市場有利於男人。負負並不會得正,我們必須同時修正兩者。
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占優勢,不平等都是很嚴重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女性在勞動市場追上男性,但男孩和男人在課堂上卻遠遠落後。一個落差正在縮小,但另一個則正在擴大。
我會先描述 K–12 (1) 教育制度中的性別落差,接著指出這些落差的主要成因:男孩和女孩的成熟速度截然不同,尤其是青春期。接著我會追查一些高等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我在這裡傳達的主要訊息是,每個階段、世界各地都有明顯的性別落差,而且有許多落差正在持續擴大。但政策制定者就像被車頭燈照到嚇呆的鹿,不知該怎麼回應。
女孩成績比男孩好
關於芬蘭,你知道什麼事情?它是地球上最快樂的國家?正確8。它的學校體系是一流的?嗯,對了一半。芬蘭的教育成果確實在國際名列前茅——但這是因為女孩子很厲害。OECD每三年會調查一次十五歲學生的閱讀、數學和科學技能。這叫做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測驗,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極大注意。芬蘭是很適合觀察教育面性別落差的國家,因為這個國家的表現非常好(的確,每次PISA結果公布之後,其他國家對芬蘭都是一陣嫉妒)。不過,雖然芬蘭學生在PISA的整體表現名列前茅,卻有巨大的性別落差:二○%的芬蘭女孩在測驗中獲得最高的閱讀分數,但男孩只有九%9。至於閱讀分數最低的學生,性別落差剛好相反:二○%是男孩,七%是女孩。在大多數的測驗中,芬蘭女孩在科學和數學方面的表現也贏過男孩。重點在於,芬蘭那享譽國際的教育表現,全都要歸功於芬蘭女孩表現太好(事實上,美國男孩的PISA閱讀測驗成績跟芬蘭男孩一樣)。
這對於湧進芬蘭、想複製其成功的教育改革者來說,或許有些含意,但它只是國際趨勢中一個特別鮮明的例子。在世界各地的國中和國小,女孩都領先男孩。OECD國家的女孩,閱讀能力領先男孩約一年;相較之下,男孩在數學上的優勢不但微薄,還正在縮小10。
男孩三個關鍵科目(數學、閱讀、科學)全部不及格的機率比女孩高五○%11。瑞典正要開始努力應付校內的「男孩危機」(pojkkrisen)。澳洲設計了一套閱讀計畫,叫做「男孩、男人、書籍、位元組」(Boys, Blokes, Books and Bytes)。
在美國校園,幾十年來都是女孩比較優秀。但她們現在的領先幅度更大,尤其是讀寫和口語技能。差距早就拉開了。如果父母因素(parental characteristics)相同,女孩五歲時「準備好入學」的機率比男孩高一四%,至於富裕和貧窮小孩、黑人和白人小孩、或有上幼兒園和沒上幼兒園的小孩之間,落差更是大得多12。四年級時閱讀能力的性別落差是六%,到八年級結束時擴大到一一%13。數學方面,四年級時男孩贏六%,但到八年級差距縮小至一%14。在一項以全國分數為依據的研究中,史丹佛大學學者西恩.里爾頓(Sean Reardon)發現,三到八年級的數學成績沒有整體落差,但英文的差異很大。「美國幾乎每個學區的女學生,ELA(英語語言藝術)測驗的表現都比男學生好。」他寫道:「在平均學區中,落差大約是成績水準的三分之二,而且比大多數大規模教育介入措施的效果更大。」15
到了高中,女生的領先已經穩固。女孩在高中成績平均績點(GPA)總是比男孩更有優勢,甚至五十年前就是這樣,即使那時女孩的外在動機明顯較低,因為她們上大學的比例和職業期望都低於男孩。而且,這個落差在最近幾十年已經擴大,如今,女孩最常獲得的成績是A,而男孩是B16;正如圖1-1所示,女孩包辦了高中成績前一○%(以GPA排名)學生的三分之二,但底層的比例剛好相反。

女孩接受進階先修課程或國際文憑課程的機率也高很多17。全國趨勢當然會掩飾地理上的巨大變化,所以把鏡頭拉近並觀察特定地區會很有用。
以芝加哥為例,最富裕社區的學生,在九年級時,平均成績獲得A或B的機率高很多(四七%),相較之下最貧困社區的學生只有三二%18。這是很大的階級落差,考量到芝加哥是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大城市,這表示種族落差也很大。但驚人的是,女孩和男孩獲得好成績的比例差異,也是四七%對三二%。如果你想知道高中一年級的成績是否重要,那麼答案是:很重要,它們預測了之後的教育成果。分析這些資料的芝加哥研究人員堅稱:「成績反映了教師重視的多項因素,而正是這種多元特質,使成績能夠準確預測重要成果。」
確實,男孩在大多數標準化測驗中,表現依然比女孩好一點。但這個落差已經急遽縮小,SAT的差異降到一三%,而ACT(2) 的差異已經消失19。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無論如何,SAT和ACT的重要性都低很多,因為大學不再採用它們當作入學條件,而這種做法無論有什麼其他優點,似乎都更加擴大了高等教育的性別落差。再舉一個性別落差的傳聞當例子:每年《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都會舉辦中學和高中的社論比賽,並且刊登獲勝者的觀點。籌辦人告訴我,申請人的女對男比例是「二比一,很可能將近三比一」20。
事到如今,就算得知男孩的高中畢業率比女孩還低,應該也不意外了。二○一八年,準時畢業(也就是註冊後四年畢業)的女孩有八八%,相較之下男孩只有八二%21。男性畢業率只比窮學生(八○%)稍微高一點。你可能會認為,這些數字很容易查到,用谷歌(Google)迅速搜尋一下就好。其實我著手撰寫這個段落的時候,也以為是這樣。但事實上,我是在布魯金斯學會弄了一個小型研究計畫才查到的,而且原因很發人深省。聯邦法律規定,州政府必須根據種族、英文熟練度、經濟劣勢、無家可歸狀態以及寄養身分來報告高中畢業率。這種資料對於評估那些輟學風險最高的群體的趨勢來說,是無價之寶。但奇怪的是,州政府不必根據性別報告結果。所以若要取得上述引用的數字,就必須搜遍每個州的資料。
有一間活躍的非營利聯盟 Grad Nation,正在試著將美國的全體高中畢業率提高到九○%(二○一七年為八五%)22。這是一個很遠大的目標。聯盟指出,若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改善「有色人種、身心障礙及低收入學生」的數值。當然,這些肯定必須改善,但他們漏了一個重要的群體——男孩;畢竟女孩跟目標值只差二%,但男孩比目標值低了八%。
男孩的大腦發展較慢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有許多種可能的解釋。有些學者將「男孩在學校的表現相對較差」跟「男孩對高等教育的期望較低」相連結,而這肯定完全符合惡性循環的定義23。有些學者則擔心女教師偏多(占四分之三,而且還在增加)會讓男孩處於劣勢24。這固然重要,但我認為我們眼前有一個更大、更簡單的解釋:男孩的大腦發展較慢,尤其是在中等教育最關鍵的那幾年。將近四分之一的男孩(二三%)被歸類為擁有「發展障礙」,因此我們合理懷疑,功能失常的並不是男孩,而是教育機構25。
在《契機年齡:從青春期的新科學中學到的教訓》(Age of Opportunity: Lessons from the New Science of Adolescence)中,勞倫斯.史坦堡(Laurence Steinberg)寫道:「高中青少年只要冷靜、休息充足,並意識到做出正確選擇就會得到回報,他們就會做出更好的決策。」26 大多數家長、或任何回想自己青少年時期的人,看到這句話時可能會回應:「勞倫斯,這我早就知道了。」但青少年根本坐不住,以至於他們很難「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們年輕的時候會半夜溜出去參加派對;等到年紀大了,我們會溜出派對回家睡覺。史坦堡展現出一件事:青春期,基本上就是大腦中尋求感官刺激的部位(去參加派對吧!別管學業了!)和控制衝動的部位(我今晚真的要用功讀書)之間的大戰。
你可以將其想成心理版本的汽車油門和剎車。青少年時期,我們的大腦會猛踩油門。我們追求新奇、刺激的體驗,年輕人的衝動控制(剎車機制)之後才會發展。史丹佛大學生物學家兼神經學家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在他的著作《行為:人類最好和最糟行為背後的生物學》(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寫道:「不成熟的前額葉皮質無法成功反制像這樣的多巴胺系統。」27 對於養育子女以及協助青少年發展自我調節策略的重要性來說,這句話帶有明顯的含意。
所以,青春期的時候我們較難克制自己。但男孩在這方面的落差比女孩大很多,因為他們的油門踩得更大力,剎車則更無力。大腦中跟衝動控制、計畫、未來導向有關的部位(有時被稱為「大腦的執行長」),多半都位於前額葉皮質內,而男孩這個部位比女孩晚熟兩年左右28。假設女孩的小腦在十一歲時長到完整大小,男孩則要等到十五歲。除此之外,根據神經科學家格克欽.阿久雷克(Gokcen Akyurek)表示,小腦「對於情緒、認知和調節能力具有調整作用」29。我懂,因為我有三個兒子,這些發現和注意力以及自我調節方面的調查證據是一致的,也就是最大的性別差異發生於青春期中期,這有一部分是因為青春期對海馬迴(大腦的一個部位,和注意力、社會認知有關)的作用30。許多青少年都聽過一個問題:「你為什麼不多像你的姊姊/妹妹一點?」這問題的正確答案大概是:「媽,因為皮層和皮層下灰質有雌雄二型性軌跡!」(回頭繼續打電動。)
雖然大腦部位需要成長,但有些大腦纖維必須削減,才能改善我們的神經功能。我們的大腦部位必須變小才能更有效率,這種概念很奇怪,卻無比真實。大腦基本上會整理自己,你可以將其想成在修剪樹籬以維持美觀,這個削減過程在青少年發展中尤其重要;有一項以一百二十一人(介於四到四十歲之間)的大腦成像為依據的研究,顯示出女孩比男孩更早開始這個過程,這個落差在十六歲左右最大31。科學記者克里斯特內爾.史托爾(Krystnell Storr)寫道:「探討大腦性別差異的研究越來越多,這些發現可說是錦上添花……科學指出我們的大腦發展方式有差異。有誰能反駁?」32(沒想到反駁的人還滿多的,但我之後再談…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