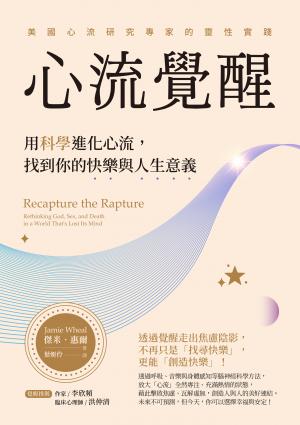我當時正飛往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前往一場「讓非洲做足準備迎接未來」的高峰會演講。我坐在觀眾席裡聽著講者描述非洲大陸的困境、挑戰和機會,既得到很多靈感也有許多疑惑——在人口稠密的城鎮導入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利用奈米科技從雲朵和海水萃取出飲用水,這些新發明帶來靈感。但我也同樣困惑,一位加州女性興奮的介紹她的專案,如何讓中非不識字的村民打造機器人,另外還有位綁著馬尾的劍橋大學研究員,在談論逆轉老化的過程,以及實現長生不死的可能性。這些不和諧的議題讓我困惑不已。
失衡的指數成長與惡化
只能自給自足的農民究竟需要機器人做什麼?在一個連讓每個人維持生活基本需求都有困難的世界裡,為少數幸運者提供無盡延長壽命的技術,會是人類發展上的最佳策略嗎?
顯然,這些專案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上,跳過了幾個階層——直接從生存需求跳到自我超越,忽略中間的各種需求(那些多數人生活和死亡之處)。
我快速瀏覽議程表,想看看還有什麼能期待的內容:指數成長的教育——只要有無線網路,每個孩子都能在各地線上學習;指數成長的生物學——拼接不同DNA並加速進化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指數成長的運輸——自動駕駛共享的應用程式與載客用的無人直升機,可減少塞車時間;指數成長的資料科學——量子運算與超光速自主演算法讓我們在行動前,就先知道我們想要什麼;指數成長的經濟——虛擬貨幣提供微型創業家資本,並有效避稅。
在這令人興奮卻又如泡沫般不真實的未來裡,一切都將踏上「指數成長」的曲線往上飆升,但有個重要的概念卻消失了——那就是指數成長的意義。如果這些專家所言不假,我們對人類經驗的所有認知,十萬年來靈長類的進化與人類文化,都會被加速變革的力量所侵蝕。哈佛生物學家愛德華.奧斯本.威爾森(E. O. Wilson)曾表示:「我們有舊石器時代的情緒、中世紀的制度和神一般的科技。」但這一切要怎麼理解,沒人給得了建議。
那個天馬行空的會議裡,每個人都把焦點放在大規模又有遠見的變化和發展上,儘管以前根本沒聽過這些辦法,可是大家都信心滿滿的認為這些作法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包括貧窮和癌症。每個人都真誠又樂觀,你在現場一定會被打動。你會跟自己說: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對的!就算違背先知的預言,又有很多人唱反調,但過去三百年來的啟蒙運動實驗一直順利的在進行。識字率在增加,人類獲得愈來愈多營養,戰爭和疾病少了,一切的指標都顯示出人類的進步沿著弧線向上。雖然這些進展很少被報導,但絕不容否認。全自動化的奢侈太空共產主義在向我們招手,儘管我們還不知道要如何從現在走到那裡。
你可以放心的做出結論:「一切都在指數型改善,不需懷疑!」
可是,當你回到家後,滑著手機看著新聞推播時,又被陷入危機的世界壓得喘不過氣:北極、亞馬遜和加州燒不盡的野火;仍在全球肆虐的疫情;敘利亞、委內瑞拉等地的難民;伊波拉病毒、新冠病毒、恐怖主義、性別主義、種族主義等各種主義,全天候都在發生。
你若無動於衷就顯得太過無情,因為一切都在以指數惡化。
經典童書《夏綠蒂的網》(Charlotte’s Web)的作者艾爾文.布魯克斯.懷特(E. B. White)曾反思道:「清晨醒來時,我總在『改善(或拯救)這個世界』與『好好享受(或品嘗)這個世界』之間掙扎。這兩股欲望相互拉扯,讓一天的規劃變得困難重重。」
即使是在最好的日子裡,試圖擎畫一個相互衝突又交錯複合的指數曲線世界,都是件相當瘋狂的事。這就像是多數人在高中時曾被轟炸過的多變量微積分,直到現在也還是不會計算。
現在,有兩條曲線正在交叉——一條是「活出生命」的曲線,另一條是「存活下來」的曲線。
「活出生命」曲線從左下角開始,愉悅的往上攀向圖表的右側。這條曲線代表個人與文化的成就,就像前述「指數成長」會議裡各種被提及的創見。如果人生是一場在海灘上的野餐旅程,這條曲線就包含要打包哪些東西、邀請哪些人、在哪裡打開野餐墊,以期獲得最好的風景。
「存活下來」曲線則從左邊開高走低,一點也不瑰麗。如果人生是一場在海灘上的野餐旅程,這條曲線就是在說要留意潮汐、注意是否有動物逃往高處,並查看狂跳訊息的手機是否發來海嘯警告。
「活出生命」沒有時間限制且樂觀,著重於增加選擇——享受這個世界。「存活下來」則被時間約束且悲觀,著重於減少選擇——拯救這個世界。現在,我們不偏不倚的落在這個黃金交叉點上,令我們難以規劃未來。

坍塌的聖堂情節
全世界都在發生指數程度的改變,但我們理解這一切的能力卻遠跟不上。更糟糕的是,我們正在目睹意義的崩解。我們每天都在透過不確定性、焦慮和困惑,體驗這種差距。就連我們最熟悉、最信任的指標性事物,如今也無法告訴我們何謂正確方向。
知名的巴黎聖母院在二〇一九年四月發生祝融之災,法國隨即宣布這是國家級緊急事件。馬克宏總統心痛的在推特(現X,後文皆保留原名稱)發文,並動員資源。在火勢控制後,時事短評紛至沓來。有些人感念消防員的勇氣和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LVMH)與聖羅蘭等精品品牌的慷慨解囊,見證了法國的國民精神。有些人則不以為然,他們公開質疑之前持續撼動教會的虐待疑雲是否將被掩蓋,而聖母院被燒毀坍塌只是個預兆,暗示著教會組織也即將崩壞。
如果聖母院大火是場意外,那位於紐約金融區的雙子星大樓在二〇〇一年的坍塌則完全不是意外。蓋達組織刻意選擇這兩棟大樓為目標,因為它們象徵西方經濟權力的中心。所以,當這兩棟指標性的摩天大樓如此不堪一擊,肯定會驚憾了全世界。而且,雙子星一倒,美國的安全感也隨之灰飛煙滅。
建築物是具體的信念崇拜,這個觀念可以協助我們思考當前的意義危機。我們都有不同程度的「聖堂情結」(The Edifice Complex),每個時代裡最顯著的建築和地標反應了當時的價值觀,它們讓我們一目了然「誰在主導時代」、「該時代最在乎什麼」。
在帝國時代,法老興建金字塔、國王興建城堡,象徵天授的統治權。中世紀時代,歐洲各地都有大型修道院和大教堂,顯示出教會的力量。十八世紀民族國家興起,議會和法院在都市規劃和天際線中占據中心的位置。到了二十世紀的企業時代,摩天大樓睥睨一切——紀念著出資興建它們的商業鉅子和銀行家。今日,知名建築師所設計的科學園區最為矚目,而權力已被發明虛擬世界的人所掌握。
儘管雙子星大樓和聖母院都是「聖堂情結」陷入危機的案例——文化的裂痕成為基礎建築中真正的裂痕——事實上,我們放眼望去所見都是善意與神性權威的崩解。不只是象徵權力的指標性建設在崩壞,背後的制度也搖搖欲墜。
***
二〇〇八年,當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知名企業破產時,沒有人能明確理解市場為何如此突然且徹底的崩潰。政治人物搶占電視螢幕譴責貪婪的中產階級消費者,責備他們不該購買自己無法負擔的豪宅。等到麥可.路易(Michael Lewis)的《大賣空》(The Big Short)等事後檢討書籍問世時,人們才發現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等金融機構,存在比想像中更多知情的自利行為和冷酷無情。
如果我們以為這類恐怖的事件,在美國歐巴馬總統簽署的《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Act)等金融改革法案頒布後,就能如法案內文所言「從此不會再發生」,那就大錯特錯了——這些事情只是轉向暗地裡進行,並移轉海外。新加坡一馬公司(1MDB)的醜聞,就是拿投資好萊塢電影和一些毫無價值的專案當幌子,明目張膽的挪用公款,吸金數十億美元,最後讓馬來西亞當時的首相納吉(Najib Razak)下台入獄。而負責管理監督一馬基金的,正是高盛集團。
惡名昭彰的古普塔(Gupta)兄弟聯合南非總統雅各.祖馬(Jacob Zuma)和全球頂尖顧問公司麥肯錫,榨乾南非國庫近七十億美元,導致南非鍰(貨幣)匯率暴跌、引發政權危機。原先在曼德拉總統帶領下,充滿希望走出種族隔離制度的過渡期,此時也飽受威脅。
若公司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利潤最大化,那麼公司願意和專制政府或腐敗企業合作就很合理。一位麥肯錫員工的匿名發文在網路上被瘋狂轉載:「如果你相信資本主義會對政府、生物圈和全世界的窮人構成生存威脅,那這間公司的角色就是共犯,而我們都是受害者。」
表面上,這些政商勾結的世界並不特別引人注意——歷史上有更多的案例,這幾樁不過是最新的幾則。在近期的分析研究中,我們還可以把億萬富翁的家族企業、私募股權支持的企業和自由主義智庫與大型宗教組織都羅列進去,這些機構在二〇二〇年新冠肺炎全球肆虐期間,從急難救助活動裡奪走了四兆美元。我們也不該忽略,許多銀行替俄羅斯寡頭和犯罪集團洗錢,總金額超過兩兆美元。這些銀行最近也登上了新聞頭條。這種事情都不該發生,但確實發生了,而且從未停止。
高盛和麥肯錫(以及德意志銀行、富國銀行〔Wells Fargo〕等諸多銀行)在最近被陸續曝光的醜聞中,彰顯了不正當行為的規模,甚至有可能徹底破壞全球自由主義的承諾。
如果我們一方面推廣要在發展中的世界投資基礎建設、承擔債務、實踐民主、整肅貪腐,另一方面卻用這些要拯救我們的承諾專案來行搶,那就是自找麻煩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暨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比多數人更了解這個全球體系的運作方式。他下了個嚴肅的結論:「人們對於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信心同時殞落了,這不是巧合,也不僅是稍微相關。新自由主義已經傷害民主四十年了……各項數字都顯示:成長在趨緩,而且大多數成長的果實只提供給最頂階層的少數人。」
***
受到抨擊的不只有華爾街的銀行家。矽谷是個充滿樂觀主義的烏托邦,在這裡,每個應用程式、每間新創企業和投資人都認真致力於「讓世界更美好」。二〇〇一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之後,尖牙股(FAANG,美國股市中五家網路科技龍頭公司,包含臉書、亞馬遜、蘋果、網飛與谷歌)透過前所未有的方式將我們與世界接上線。
在這個創新的新時代裡,未來的無限憧憬令人沉醉。谷歌人不像一般上班族,他們踩著五顏六色的自行車,宣揚著「不做惡」(Don’t Be Evil)的公司口號(該口號現已刪除)。臉書剛起家的時候,是常春藤盟校精英之間的通訊錄,而開放之後,所有人都可以在網路上追蹤舊情人,並用修圖軟體美化我們的生活。
亞馬遜一鍵配送的便捷讓人成癮,摧毀許多小型企業和都市核心商場,商品可以在四十八小時或更短的時間內送達家門,實在太美妙、太愉快、太方便,讓我們得以忽略全球各地的血汗工廠與物流中心,都只支付最低工資。臉書創辦人祖克柏鼓勵我們:「快速行動,打破現狀!」一切都如此不可思議,讓我們相信所有充滿創意的破壞,最後都會有好的結果。
這一切,在二〇一六年開始改變。首先,英國脫歐的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都爆出醜聞,打擊我們對社群媒體平台的理解,發現隱匿其中的缺點——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把數百萬臉書帳號轉化為武器,刻意針對用戶提供分化的訊息。剛開始,大家並不清楚臉書知情的程度,也不知道劍橋分析公司是否僅為個案。臉書是不是一直向第三方開發者兜售我們最私密的訊息?劍橋分析公司有哪些行為是惡意的?哪些行為得到了完全的許可?
這似乎都不重要了。民主還沒有從近期的兩場選舉結果中復活,接下來的幾場選舉也很難恢復真正的民主精神。民主經歷了內戰、納粹和蘇聯,卻不敵廣告關鍵字和推特…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