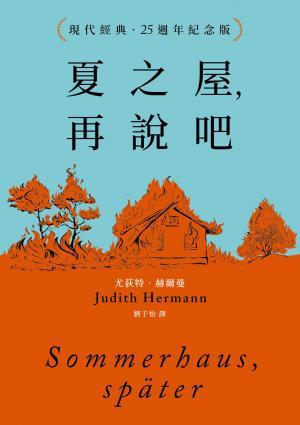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做心理治療,就賠上我的紅珊瑚手鍊以及我的情人。
紅珊瑚手鍊來自俄國,精確來說是來自聖彼得堡,已超過百年歷史,我曾祖母曾將它戴在左手手腕上,它還殺死了我曾祖父。我是要講這個故事嗎?我不確定,真的不太確定:
我的曾祖母非常漂亮。她跟曾祖父去了俄羅斯,因為曾祖父去幫俄國人蓋工業爐。曾祖父將曾祖母安置在聖彼得堡瓦西里島上的一間大公寓,這個島是由大小涅瓦河沖積而成。若曾祖母踮著腳尖,從這間位於馬里吉大道的公寓窗口看出去的話,可以看到河流及喀琅施塔得灣。但曾祖母不想看河,不想看喀琅施塔得灣,也不想看馬里吉大道上漂亮的房子。曾祖母根本不想看窗外,她拉上厚重的紅天鵝絨窗簾,關上房門,地毯吸去所有的聲響,曾祖母只是坐在沙發、扶手椅或四柱床,身子前後搖晃,想念著德國的家。馬里吉大道偌大的公寓裡,光線猶如暮色般昏暗不明,就像深海底的光。或許曾祖母覺得這些陌生、這個聖彼得堡及整個俄羅斯,都不過只是個深沉混沌的夢,很快她就會從夢中醒來。
但我曾祖父卻走遍整個國家,到處幫俄國人蓋爐子。他蓋了豎爐、焙燒爐、火焰反射爐、步進式加熱爐,還有利佛摩爾爐。他總是離開很久,會寫信給曾祖母。每回收到信,曾祖母就稍稍拉開窗前厚重的紅天鵝絨窗簾,退幾步,就著透過來的一束窄窄的日光讀信:
我跟妳解釋一下,我們在這裡蓋哈森克雷夫爐,是由好幾個蓄熱室組成,蓄熱室之間透過垂直的通道互相連接,並以爐篦式燃燒的火焰加熱──妳一定還記得我在霍爾斯坦布倫舍維爾德尼斯(Blomesche Wildnis)蓋的坩堝爐,當時妳特別喜歡──哈森克雷夫爐也是一樣,礦石會從開口送達最上面的爐篦……
讀這些信令曾祖母感到非常疲倦,她不記得布倫舍維爾德尼斯的坩堝爐,但她記得布倫舍維爾德尼斯,記得那裡的牧場以及平坦的地勢,記得田野上推成圓柱形的乾草堆,以及夏天蘋果酒甜甜冰涼的味道。她讓房間重新陷入暮色般的昏暗,疲憊地躺在沙發上,喃喃地唸著:「布倫舍維爾德尼斯,布倫舍維爾德尼斯……」聽起來就像一首童謠,一支催眠曲,真是悅耳。
在那些年中,住在聖彼得堡瓦西里島上的除了外國商人及他們的家眷之外,還有很多俄國藝術家及文人。無可避免的,他們全聽說有個德國女人,美麗、蒼白,有著閃亮的金髮,住在馬里吉大道上,幾乎總是單獨一人躲在房間裡,那麼暗,那麼柔和又冰涼,猶如大海一般。這些藝術家及文人開始登門造訪,曾祖母用她疲憊纖細的手招呼他們進來,她不怎麼說話,幾乎聽不懂別人在說什麼,只是透過低垂的眼皮緩慢如作夢般看著他們。這些藝術家及文人在柔軟的沙發及扶手椅坐了下來,陷在厚重的深色布料裡,女僕端來加了肉桂的紅茶,以及藍莓黑莓做成的果醬。曾祖母用俄式小茶爐溫暖她冰冷的手,她太累了,累到沒力氣請藝術家及文人離開。於是他們就留下來了。他們看著我的曾祖母,在昏暗的光線下,曾祖母成了某種悲傷、美麗、陌生的象徵。而悲傷、美麗、陌生正是俄羅斯靈魂的精髓,這些藝術家及文人愛上我曾祖母,我曾祖母也讓他們愛她。
曾祖父總是離開很久,於是曾祖母就讓自己被愛很久,她很小心,很謹慎,幾乎不犯任何錯誤。她用俄式小茶爐溫暖她冰冷的手,用情人火熱的心溫暖她冰冷的靈魂。她學會從輕柔陌生的語言中聽懂一些詞彙:「妳是最溫柔的白樺。」就著窄窄一束日光,她讀著那些關於熔爐、德維爾式爐及管式爐的信,然後統統丟進火爐燒掉。她讓別人愛她,夜裡入睡前哼唱著布倫舍維爾德尼斯,當她的情人好奇地望著她時,她只是微笑,沉默著。
曾祖父承諾很快就會回來,很快就會帶她回德國。但他並沒有回來。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聖彼得堡的冬天過了,而我曾祖父仍然在俄羅斯遙遠的另一方,忙著蓋爐子,曾祖母仍然繼續盼望能回到德國。她寫信到西伯利亞針葉林,他回信說很快就會回來,只要再離開一次,就最後一次了──然後,然後,他保證,就會踏上歸途。
曾祖父回家的那天晚上,曾祖母坐在臥室鏡子前梳著金髮。鏡子前有個小盒子,裝滿了情人送給她的禮物,格里戈里送的胸針,尼基塔送的戒指,阿列克謝送的珍珠及天鵝絨絲帶,葉梅利揚的一束捲髮,米哈伊與伊利亞的勳章、護身符及銀手鐲。盒子裡還有尼可萊.謝爾蓋耶維奇的紅珊瑚手鍊,六百七十五顆小珊瑚串在絲線上,如怒火般殷紅。曾祖母將梳子放在大腿上,閉上眼睛好一陣子,當她再睜開眼睛後,便拿出盒子裡的紅珊瑚手鍊戴在左手手腕上,她的膚色極為蒼白。
那天晚上她與曾祖父三年來第一次共進晚餐。曾祖父說著俄文,對著我曾祖母微笑。曾祖母放在大腿上的雙手交疊手指互握,朝著我曾祖父微笑。曾祖父說起大草原、荒野以及俄羅斯白夜,還說到各種爐子並叫著曾祖母的德文名字,於是曾祖母點頭微笑,彷彿一切都聽懂了。接著曾祖父繼續用俄語說他必須再去一趟海參崴,邊說邊用手抓起餃子吃,用手擦著油膩的嘴角,他說,海參崴是最後一站,然後該是回家的時候了,回德國,還是,她想繼續待在這裡?
曾祖母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但她聽懂了海參崴,於是她抬起手放在桌面上,紅彤彤如怒火般耀眼的紅珊瑚手鍊在她蒼白的左手手腕上閃閃發亮。
曾祖父瞪著紅珊瑚手鍊,將吃到一半的餃子放回盤子,用麻布餐巾擦手,揮手叫女僕離開房間,用德文說:「這是什麼?」
曾祖母說:「一條手鍊。」
曾祖父說:「假設我有資格問妳的話,哪來的手鍊?」
曾祖母輕軟低聲說:「我非常期待你問,這是尼可萊.謝爾蓋耶維奇送我的。」
曾祖父又將女僕召進來,叫她去找他的朋友伊薩克.巴魯夫。伊薩克.巴魯夫來了,駝著背,看起來半睡半醒,滿臉困惑,當時夜已很深,他尷尬地不停用手梳理一頭亂髮。曾祖父與伊薩克.巴魯夫激動地在房間內走來走去,不斷地討論,伊薩克.巴魯夫試著說些安撫的話語但無濟於事,那些話令我曾祖母想起她的情人。曾祖母無力地倒在柔軟的單人沙發,冰冷的手握住俄式小茶爐。曾祖父與伊薩克.巴魯夫用俄語交談,曾祖母只聽懂了「副手」及「彼得羅夫斯基公園」這兩個詞。女僕受命拿著信出門走進黑夜。當天色終於微亮,我曾祖父與伊薩克.巴魯夫也出了門,曾祖母在柔軟的單人沙發中睡著,她纖細的手腕戴著紅珊瑚手鍊無力地垂掛在扶手上,房間裡如此昏暗寂靜,如同海底一般。
接近中午時分,伊薩克.巴魯夫回來了,打躬作揖地向我曾祖母致哀,告知她我曾祖父已在清晨八點逝世,尼可萊.謝爾蓋耶維奇在彼得羅夫斯基公園的小山丘上一槍射進曾祖父的心臟。
我曾祖母等了七個月,最後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日,也就是革命開始的第一天,將我祖母帶到這個世界,然後打包行李回到德國。她搭上的那班開往柏林的列車,據說是最後一班離開聖彼得堡的火車,之後鐵路工人罷工,俄羅斯與國外的交通全部中斷。當火車車門關起,火車頭將白煙吹入冬日的寒空時,月台盡頭出現伊薩克.巴魯夫彎腰駝背的身影。我曾祖母看著他過來,便請求列車長等他一下,於是伊薩克.巴魯夫在最後一分鐘蹣跚地爬上德國列車。往柏林的漫長旅程中他陪在我曾祖母身邊,幫她提行李,拎著帽箱及手提包,不厭其煩地一次又一次地向她表達他終身的感激。我曾祖母只是看著他微笑,一言不發;她左手手腕戴著紅珊瑚手鍊,而我祖母小小的身軀睡在柳條籃裡,那時候便已看出,比起我曾祖父,她長得更像尼可萊.謝爾蓋耶維奇。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做心理治療,就賠上我的紅珊瑚手鍊以及我的情人。
我的情人大我十歲,像條魚一樣。他有魚灰色的眼睛,魚灰色的皮膚,就像隻死魚一樣,整天躺在床上,冰冷沉默。他覺得很不舒服,整天癱在床上,就算開口也就只有這麼一句話:「我對自己不感興趣。」我是要講這個故事嗎?
我不確定,真的不太確定。
我的情人是伊薩克.巴魯夫的曾孫,在他細細的血管裡流著俄國及德國的血。伊薩克.巴魯夫一生忠於我曾祖母,卻娶了她的波美拉尼亞女僕。他們一共生了七個孩子,這七個孩子生了七個孫子給他,其中一個孫子又給了他唯一一個曾孫,也就是我的情人。他的父母在盛夏暴風時淹死在湖中,我曾祖母要我去參加他們的喪禮──聖彼得堡往事的最後證人就要長眠於布蘭登堡的土地下,與之掩埋的,還有她自己不願再提起的往事。因此我去了伊薩克.巴魯夫孫子夫婦的葬禮,我的情人站在他們的墓碑旁,掉了三滴灰色的眼淚。我將他冰冷的手握在我的手裡,當他回家時,我也跟著他走。我以為自己可以用聖彼得堡的故事來安慰他;我以為,他可以告訴我這個故事的另一種版本。
但我的情人不說話。他也不要聽,他完全不知道一九〇五年那個冬天清晨,我曾祖母曾讓火車停下來,讓他曾祖父能逃離俄羅斯,在最後一秒鐘。我的情人只是癱在床上,就算開口也就只有這麼一句:「我對自己不感興趣。」他的房間很冷又布滿灰塵,窗外就是墓園,墓園總是不斷傳來喪鐘的聲音。若我踮起腳尖往窗外看,可以看到剛挖開的新墳、康乃馨花束及哀悼的人。我常常坐在房間角落地板上,屈起膝蓋貼著身體,輕輕地將灰塵吹得滿室紛飛。我非常訝異有人會對自己不感興趣,像我就只對我自己感興趣。我看著我的情人,我的情人看著他自己的身體,像個死人一般。有時我們會像仇敵一般做愛,我咬他鹹鹹的嘴,覺得自己彷彿瘦到不成人形,儘管我根本不是,我可以假裝我不是我。陽光透過窗前樹木照進來是綠色的,水亮水亮的,像在湖邊一樣,而滿室紛飛的灰塵猶如水藻。
我的情人很哀傷,我同情地問他,是否不該跟他講那個俄羅斯的小故事,我的情人高深莫測地回我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他不想聽,而且我根本不該將自己的故事跟別人的故事混為一談。我問:「那你有自己的故事嗎?」他說沒有,他沒有故事。但他每週去看醫生兩次,是個臨床心理師。他不准我陪他去,也拒絕告訴我任何關於心理師的事,他說:「我訴說我自己,就這樣。」當我問他是否會提到他對自己沒興趣一事,他滿臉不屑地看著我,沉默不語。
我的情人沉默,或者只說那句話。我也跟著沉默,然後開始想著心理師的事。我的臉一直像我的腳板一樣沾滿灰塵,我想像自己坐在心理師的房間訴說自己。我無法想像自己有什麼好說的,自從我開始待在我的情人身邊後,就不怎麼說話了。我幾乎不跟他說話,他也根本不跟我說話,總是那一句而已。有時,我甚至會以為所謂語言不過就只是那八個字而已:我對自己不感興趣。
我開始常常想著心理師,我只想著在他那個陌生房間裡談話,而那很舒服。我二十歲,無所事事,左手手腕上戴著紅珊瑚手鍊。我知道曾祖母的故事,我能神遊般地想像自己走在馬里吉大道暮色般昏暗的公寓裡,我從祖母的眼睛看到尼可萊.謝爾蓋耶維奇。過去的故事與我糾結纏繞,有時彷彿就是我自己的經歷,曾祖母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只是,沒有曾祖母的我的故事在哪裡?我不知道…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