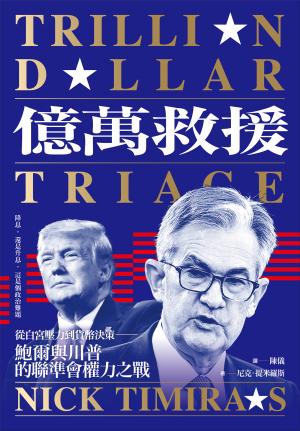傑洛米.鮑爾在馬里蘭州的切維崔斯(Chevy Chase)長大,在家中的六名子女中排行老二。位於華盛頓特區附近的切維崔斯距離聯準會總部大約只有十一公里遠,那裡處處可見鱈魚角風格的住宅,是個風景如詩如畫的城鎮。
鮑爾出身當地的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切維崔斯會(Chevy Chase Club)在當地頗負盛名,鮑爾一家是第一批加入的天主教家庭,而他的父親(也叫傑洛米)後來更是成為切維崔斯會的會長。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老鮑爾曾以歐洲陸軍步兵的身分參戰,並親身經歷過激烈的肉搏戰。戰爭結束後,他開啟律師職涯,曾在幾場勞資糾紛中代表公司方發聲,並在這個專業頗有成就。鮑爾正是從他父親的身上學會了謹言慎行。鮑爾的母親派翠西亞.海頓(Patricia Hayden)畢業於華盛頓三一學院,曾代表她那一屆畢業生致告別詞;畢業後,她加入陸軍地圖服務部門,擔任統計人員的工作。和老鮑爾結婚後,她開始廣泛從事志工活動,並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裡兼職。
家人習慣叫鮑爾「小傑鴉」,長大後的小傑鴉追隨父親的腳步,到喬治城預備中學唸書,那是一所位於貝賽斯達(Bethesda)的耶穌會高中男校。在那求學的學生必須依規定穿上正式外套、打上領帶,每天還得參加彌撒;就算只是像上課遲到這種非常輕微的違規行為,都會被處罰,違規者得去名為「上帝審判所」的留校觀察室閉門反省。喬治城預備中學出了許多未來的外交官、眾議員和參議員,還有川普最早提名的兩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尼爾.戈蘇奇(Neil Gorsuch)以及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學生時代,鮑爾人氣很旺,他是喬治城預備中學美式足球隊「小驚嘆」(Little Hoyas)的中鋒,也是一名好學生。當過兩任佛羅里達州眾議員的共和黨人法蘭西斯.魯尼(Francis Rooney)是他高中同班同學。憶起當年,鮑爾說,魯尼擁有「殺手級的聰明才智」。
儘管鮑爾擁有一流的教育背景——一九七五年從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畢業,主修政治——他卻認為自己有點大器晚成。畢業那年夏天,他拎著一把吉他遊歷歐洲,還在巴黎的某間餐館,以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的〈我寂寞到想哭〉(I’m So Lonesome I Could Cry)一曲和其他民謠,和在場的群眾同樂。回到華盛頓後,他在父親友人開的辦公室用品公司謀得一個差事,後來又去擔任某參議員在國會山莊的助理。眼看著往昔的同班同學個個從事既體面又高薪的工作,他決定前往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學院深造,並在那裡找回從前的幹勁。
從喬治城大學畢業後那幾年,鮑爾陸續在曼哈頓幾家聲譽卓著的法律事務所擔任職員,最後在一九八三年轉換跑道,加入投資銀行業的狄龍瑞德公司(Dillon, Read & Company),這家公司的老闆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新英格蘭人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布雷迪為人低調,但人脈非常廣闊。
加入狄龍瑞德公司兩年後,一九八五年,鮑爾和哈佛大學畢業的科學電視節目製作人暨編劇艾莉莎.李奧納德(Elissa Leonard)結婚,她是他妹妹的朋友。婚後,李奧納德保留她本來的姓氏,不過,在老大和老二出生後(他們共育有三名子女),她還是暫時放下了原本的職業生涯。
在狄龍瑞德公司任職時,鮑爾搞砸了布雷迪的一場會議,當時他介紹自己是土生土長的華盛頓人,對公共服務有興趣,願能竭盡全力為公司效勞。狄龍瑞德公司的同事聽到他的自我介紹後,都不由得直翻白眼:他花在華盛頓的時間可說是白白浪費了,因為那些經歷對創造銀行業務根本沒有幫助。不過,鮑爾並不以為意,而他和布雷迪之間的聯繫(華盛頓)事後也終於有了回報。
幾個月後,人稱「油神」的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對石油出口商優諾科公司(Unocal Corporation)展開敵意收購,狄龍瑞德公司為了捍衛優諾科公司,不惜與皮肯斯槓上。布雷迪致電要鮑爾前往華盛頓,陪他和財政部、白宮與國會的幾位高官開會。
後來,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為了檢討一九八七年黑色星期一股市崩盤事件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並任命布雷迪擔任小組主席。不久後,雷根又提名他擔任財政部長。布雷迪才剛上任幾個月,他的朋友喬治.布希(George H. W. Bush,注:老布希)就當選美國總統。這對鮑爾來說似乎是個大好機會,不過,布雷迪已事先同意不帶他公司的人馬進駐華盛頓特區,這令鮑爾大失所望。
兩年後,狄龍瑞德公司一位合夥人走進鮑爾的辦公室,他說,布雷迪正在尋找一位新助理部長:「布雷迪希望找一位像傑伊.鮑爾的助理部長。」鮑爾建議了幾個人選,不過,他最後補了一句話:「但他幹嘛找廉價的複製品?直接找我不就得了?」
就這樣,鮑爾成了布雷迪的助理部長。幾個月後,鮑爾打電話給他在華爾街的前東家達維律師事務所(Davis Polk & Wardwell),希望對方推薦一位肯賣力工作的助理給他。事務所推薦了當時年僅三十三歲的奎爾茲,他是長春藤名校畢業的律師。鮑爾錄用了這名年輕律師,並自此開啟另一位未來的聯準會同事之公共政策職涯。
金融危機
對於一個剛加入美國財政部的官員來說,一九九○年絕對不是好過的一年。在那之前的幾年間,美國反覆受到不同的金融崩潰與金融墮落行為打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儲蓄貸款機構危機,已導致超過一千家銀行與存款機構倒閉,狀況直到一九九○年年底仍未全面受控。保護銀行存戶存款的保險基金全數耗盡,經濟也陷入衰退。
然而,這卻是透過第一手經驗,學習如何應對不可預測危機的絕佳時機。一九九一年年初,鮑爾陷入一場和新英格蘭銀行(Bank of New England)有關的災難風暴中心,當時,這家大型區域性銀行正因商用與住宅不動產市場崩盤而處於倒閉邊緣。鮑爾與其他監理人員不斷苦思紓困的潛在後果。立即可見的風險並不是大到無法收拾,畢竟新英格蘭銀行只是美國第三十三大銀行。不過,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和花旗集團(Citigroup)或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陷入無力償債處境時的問題一模一樣。新英格蘭銀行與兩家姊妹銀行的存款共有一百九十億美元,金額遠遠超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簡稱FDIC)的擔保金額。兩條路線擺在眼前:(一)政府應該任由這些經營不善的機構被市場淘汰;或者(二)政府有責任防堵這些機構的問題,以免它們的問題進一步衝擊到更廣大的經濟體系。
鮑爾的直屬長官羅伯.格勞伯(Robert Glauber,他是哈佛學者)堅定選擇了第一個選項:他痛恨紓困。格勞伯用力捶著財政部會議室的桌子,同在會議室裡的鮑爾和聯準會理事約翰.拉威爾(John LaWare)只能無奈地瑟縮在一旁。憤怒的格勞伯堅持,存款人必須接受存款縮水、並為銀行的過失買單的命運。如果我們老是出面救援,一定會製造「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他所謂的「道德風險」是保險業的用語,用來形容明明知道自己因為有保險保障(所以不會產生更大損失),而蓄意承擔風險的人。
格勞伯說完長篇大論後,拉威爾平靜地闡述了聯準會的立場:「你代表政府,你絕對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但我們認為,如果要求那些不受保障的存款人接受存款縮水的命運,一定會發生嚴重的後果。美國每一家銀行在星期一開門營業後,絕對會發生擠兌,到時候,每一家貨幣中心型(money-center bank)的銀行業者勢必會跑來向我們求助。你真心有膽試試看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嗎?」
由於害怕爆發更大的危機,紓困相關的疑慮就這麼被暫時擱置了。
而鮑爾說:「我們無異議選擇第一條路。」1
加碼賭注
幾個月後,鮑爾再次因相同的問題而傷透腦筋:當金融機構即將陷入無力償債的境地,應該如何處置?不過,這次的問題牽涉到更大的利害關係。一九八○年代期間,所羅門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在財務與文化上叱吒華爾街(這家投資銀行向來是獲利能力最高的企業之一)。湯姆.沃夫(Tom Wolfe)在一九八七年創作的諷刺小說《走夜路的男人》(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小說的主人翁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債券銷售人員)就是以該公司為虛構的背景;此外,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在一九八九年創作的《老千騙局》(Liar’s Poker,這本書對受睪固酮驅動的交易文化做出了尖銳的批判)一書,更是直接取材自該公司的真實場景。但是到了一九九一年,隨著華爾街的狂熱派對突然轉變成嚴重的宿醉,原本看似無所不能的所羅門兄弟公司,也終於夜路走多了,必有遇鬼時。
從那年的五月底開始,這家債券交易巨擘的問題就已隱約浮現。當時,所羅門兄弟公司藉由壟斷市場,逼迫那些被美國公債標售市場拒於門外的經紀商(以及原本賭價格將下跌,並因此放空那類證券的套利操作者),以較高的價格向所羅門兄弟購買國庫票據。於是,聯邦監理機關開始調查所羅門兄弟和幾名客戶究竟耍了什麼手段,才能控制幾乎九四%的兩年期國庫票據(Treasury notes)市場。
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是代美國財政部在市場上執行交易的機構,所羅門兄弟公司則是獲准能與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直接進行交易的三十九家「初級市場交易商」(primary dealers,注:又稱主要交易商)之一。通常來說,初級市場交易商會直接向政府購買美國公債,再將這些證券轉手賣給其他投資者。每一個向政府購買債券的買家,都必須遵守總購買金額上限的規定。不過,所羅門兄弟公司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以客戶的名義向政府購買美國公債,藉此規避前述的購債金額限制,進而把它利用多位客戶名義購入的證券集合在一起,達到壟斷市場的目的。
隨著監理機關持續深入調查,所羅門兄弟公司的高階執行主管為了擺脫這些醜聞,抓了一名資深交易員來當替死鬼;根據他們披露的資訊,這名交易員藐視政府規定,操縱債券投標作業。規模高達兩兆兩千億美元的美國公債市場隨著這些醜陋的情事被揭露而興起波瀾。有太多疑問還需釐清,包括:是否有其他交易商和所羅門兄弟公司一同操縱訂價?為什麼所羅門兄弟公司沒有早一點坦白這些事?美國政府是否因這項操縱行為,而莫名支付了較高的聯邦債券利率?還有,為什麼監理機關沒有早一點注意到這個弊端?
在餘波蕩漾的混亂局勢中,紐約聯邦準備銀行將所羅門兄弟公司的傳奇執行長兼董事長約翰.加弗蘭德(John Gutfreund)掃地出門。2 政府也謹慎審酌更嚴苛的罰則,暫時撤銷了該公司在美國公債領域初級市場交易商的特許地位;即使政府債券交易占所羅門兄弟公司總營收的比重不高,但在公司債權人眼裡,政府的懲罰形同對這家公司判了死刑。所羅門兄弟公司平日就高度仰賴短期借款來支應交易業務所需的資金。如果聯準會切斷所羅門兄弟的業務生路,債權人有可能會拒絕對它承作新的貸款,進而逼得公司為了籌措資金而廉價拋售手上的資產,屆時,這家傳奇企業幾乎肯定會走上破產一途。
向來備受推崇的投資人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是所羅門兄弟公司當時最大的股東,他同意接下公司董事長一職,協助收拾這個殘局,期盼能安撫動盪的市場。不過他也強調,如果財政部決定不讓所羅門兄弟公司保有它和聯準會之間的特許關係,他就會辭去董事長。於是,一場涉及重大利害關係的邊緣政策戰就此展開。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星期日當天,鮑爾接到金融圈幾位最有權勢的大老級人物的一連串緊急電話,包括布雷迪、葛林斯潘、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葛瑞德.柯里根(Gerald Corrigan),以及巴菲特。這些大老全是為了和他討論華爾街最呼風喚雨的企業之一——所羅門兄弟——的命運而來電。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情況急如星火。所羅門兄弟公司的董事會預訂在那天下午開會,推選人稱奧馬哈先知的巴菲特擔任公司董事長,董事會也已發了通知,說他們將在下午兩點三十分召開記者會,發布這項人事消息。不過,巴菲特還在舉棋不定,因為就在那天早上,財政部宣布將依照原訂計劃制裁所羅門兄弟公司,也就是要撤銷它初級市場交易商的地位。
巴菲特只是為了增強外界對公司的信心,才同意接下董事長一職,他並不想處理這個爛攤子。他說:「我絕對不會把餘生全部用來收拾這場史上最大的金融災難。」3
柯里根認為巴菲特是在虛張聲勢,他推斷,巴菲特可是所羅門兄弟公司最大的股東,不可能就這麼放任他的股票化為烏有。他也認為,巴菲特誇大了初級市場交易商地位遭到撤銷的後果。
巴菲特講了一個不堪的比喻,來表明他並沒有意願插手破產的所羅門兄弟公司:「這就好像下午兩點鐘,有位法官正打算在曼哈頓的某處悠悠哉哉、邊吃爆米花邊看棒球,而你卻大剌剌地闖進去告訴他,嘿,我們幫你把鑰匙送過來了,從現在開始,這處歸你管。還有,順帶一提,你懂日本的法律嗎?因為我們欠了日本一百億還是兩百億美元之類的。」4
鮑爾本人對於嚴懲所羅門兄弟一事抱持遲疑的態度。他心知肚明,財政部並沒有處理那麼大型的企業破產案的腹案。更何況,萬一巴菲特的看法正確,又該怎麼辦?萬一所羅門兄弟公司召開董事會後,沒有宣布新任董事長人選,東京的交易員會不會在美國時間的晚上開盤時,拒絕展延對這家投資銀行的貸款,並引發一連串的不良連鎖反應?
那個星期日,巴菲特對布雷迪發動了最後一波情感攻勢… 閱讀完整內容
書摘精選 > 鷹派、鴿派與小傑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