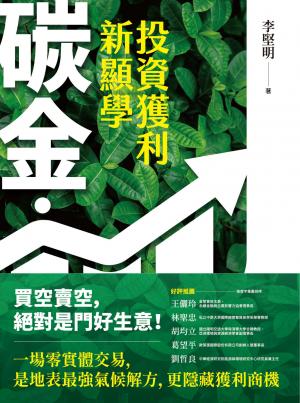碳市場將成為全球明星級產業,碳權(Carbon Credit)亦將成為重要資產與投資標的,成為日常生活一環。國際碳權威機構(Carbon Credit.com)的最新研究顯示,2018年至2021年碳權投資報酬率587%、比特幣142%、那斯達克106%、黃金僅有37%,碳權報酬率完勝其他資產。
全球淨零轉型需要投入龐大的資源與成本,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2022 年3月發布的「2050年淨零轉型計畫」,當中規畫2030年需投入超過新台幣9,000億元預算。然而,碳交易制度是觸動整體經濟社會淨零最省錢的方式, 換言之不僅可大幅節省人民的納稅錢,更能降低企業的減碳成本。
臺灣碳權交易所(Taiwan Carbon Solution Exchange, TCX)已於2023年8 月9日掛牌,並於2023年12月22日正式交易,完成8.8萬公噸國際高品質碳權,成交金額約80萬美元。碳交易已成為一門新顯學,然而碳交易的學理基礎是什麼?碳權如何產生?碳價如何決定?碳權品質好壞如何辨識?碳權投資為何必須是報酬率愈低,才值得投資?
「寇斯定理」:探索碳交易的學理基礎
全球2022年約排放574億公噸溫室氣體1,截至5月,累積在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約421ppm,雙雙達歷史新高。這也導致地表平均溫度逐年提高,2023 年的地表平均溫度更創下近12萬年歷史新高點。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成為典型的環境外部性(Externality) 2問題。
早在1960年代, 著名經濟學者羅納德. 哈里. 寇斯(Ronald Harry Coase)指出,當環境或資源出現稀少性(如全球暖化問題更嚴重),這時政府可採取斷然措施,限制經濟活動的環境或資源使用量,如核發排放額度(Allowance),限制企業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控制大氣溫室氣體濃度持續累積目的。
當政府核發排放額度限制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時,有些廠商的排放額度會不足(如晶圓廠),有些廠商的排放額度會有剩餘(如綠能產業),因此形成排放額度交易。透過排放額度的有價化(或稱價格發現),減碳成本較低的公司會得利,激勵大量減排;減碳成本較高的公司則不利,於是會以購買較便宜的排放額度方式,抵銷減排量的不足。這樣,同時能激勵減碳技術發展, 整體社會最終也會以最低的減碳成本,達到環境總目標。這個現象就是著名的「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
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s Trading Scheme)便源於「寇斯定理」,透過排放權分配,並建立交易所,藉由價格訊號(或價格發現),引導低碳科技研發,讓創造低減碳成本的廠商獲利,以降低整體經濟減碳成本,稱為「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3 ─這便是「寇斯定理」的真諦。這個偉大的發明,也讓寇斯榮獲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他對交易成本、財產權和經濟制度在複雜經濟結構中的相關運行做出清楚闡述。
為什麼碳交易會省錢?「成本有效性」的意義
2021年之後,全球淨零發展趨勢更加凸顯碳交易的重要性。《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8次締約國會(2023)的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 更直接指出,建立全球碳市場可促進國際減碳合作,開發更多減碳計畫與潛力,以及激勵減碳投資與技術研發,提升各國「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及助力《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控制溫升1.5℃全球目標的達成。
為什麼碳交易會省錢,又如何省?大家應該都知道,成本低、品質好的商品會在市場銷售,這就是確保整體社會省錢的來源。在碳交易制度下,擁有低碳科技與技術者(例如綠能、節能或碳捕獲技術),減碳成本較低,透過減碳可獲利,於是負起整體社會的主要減碳工作,形成一種專業分工現象, 降低整體社會減碳成本。
更簡單地說,碳交易就是「你減碳,我購買」,本質就是合作減碳。在「碳有價化」的前提下,以歐盟2023年為例,平均碳價介於80至100歐元/ 公噸之間浮動,那麼,有能力減碳或減碳成本較低的人(例如低碳科技研發或擁有者,減碳成本低於80歐元/公噸)會透過多減碳得利,稱為「綠色紅利」(Green Bonus);反觀減碳成本較高的人(減碳成本高於100歐元/公噸) 則傾向直接購買碳權,結果就是互蒙其利的商業行為。各位應該已發現,碳交易制度中、在市場任一碳價水準下,都由減碳成本低者負責整體社會的減碳工作,這就是碳市場的減碳與省錢奧妙處。
碳交易最終將體現最省錢的方式達到淨零轉型目標,而「成本有效性」,可謂碳交易最核心價值。傳統經濟學告訴我們,要達到「成本有效性」條件,必須所有廠商的邊際減排成本(Marginal Abatement Cost,係指增加1 單位減排量所增加的總減排成本)均相等,此時,整體社會達到特定減排目標下,總減排成本最小。舉例如下:
假設社會上僅有2家代表性廠商(台北公司與台灣公司),欲達到整體社會減排15公噸CO2e4目標。如下圖1-1所示,台北公司的減排量愈多,邊際減排成本遞增;台灣公司的減排量愈多,邊際減排成本遞增。

以下將區分2種情況,分別是直接指定減排量(沒有實施碳交易),以及實施碳交易2種情況,比較兩者達到相同減排目標之總成本差異,以凸顯碳交易低成本的優越性。
•直接管制:
假設台灣公司被要求減排7公噸CO2e,總減排成本為A的面積。若台北公司被要求減排8公噸CO2e,那麼總減排成本為B+C+D的面積,兩公司達到減排15公噸溫室氣體目標,合計付出的總減排成本為A+B+C+D 之面積(上頁見圖1-1)。
•直接管制搭配碳交易:
如果政府允許廠商間可自由進行碳權交易,假設碳價水準為500元/公噸CO2e,且減量額度(或稱碳權)可以交易,由於台灣公司減排7公噸CO2e的邊際減排成本為300元/公噸CO2e,低於碳價500元/公噸CO2e,因此台灣公司每多減排1單位,可賺取200元/公噸CO2e,增加減排誘因;然而隨著減排量增加,邊際減排成本提高,直到收支平衡為止,如圖1-1之a點。由此可知在碳交易機制下,台灣公司的減排量相較於直接指定的7公噸CO2e 多減排3公噸CO2e,增加減排至10公噸CO2e,總減排成本為A+B面積。
反觀台北公司,由於碳價水準高於邊際減排成本(如圖1-1之a點之1,000元/公噸CO2e所示),因此台北公司會向台灣公司購買碳權,抵換其減排量的要求,並隨著減排量減少,邊際減排成本降低,直到收支平衡為止,如圖1-1之a點。由此可知,在碳交易機制下,台北公司的減排量由直接指定的8公噸CO2e減少至5公噸CO2e,總減排成本為C面積。兩公司共同努力,達到15公噸CO2e減排量,而合計總減排成本為A+B+C之面積(見圖1-1)。
比較上述2種制度,雖然均可達到減排15公噸CO2e溫室氣體目標,然而搭配排放交易的總減排成本(A+B+C之面積),則低於直接管制(沒有搭配碳交易)的總減排成本(A+B+C+D之面積),可證明搭配排放交易具「成本有效性」的優越成果。
因應全球淨零,企業將面臨昂貴的排碳成本及承擔「碳風險」(Carbon Risk),成為永續經營的最大挑戰。而碳交易制度,不但可幫國家省錢(「成本有效性」),同時體現碳成本公平負擔;易言之,碳交易制度不但具經濟效率,同時也促進公平正義。
一份由國際碳交易協會(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IETA)於2023年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為達到2030年減碳目標,如果各國獨立執行減碳投資,則減1公噸碳的成本約130美元/公噸CO2e;如果合作減碳,則減1公噸碳的成本約27美元/公噸CO2e,兩者差距5倍之多,證明施行碳交易可節省巨幅減碳成本。這就是為什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要提出「京都機制」(Kyoto Mechanism)與「巴黎機制」(Paris Mechanism),呼籲國際減碳合作的主要原因。
「京都機制」:全球減碳合作的推手
全球近200個國家合計排放約574億公噸溫室氣體至大氣層,其中,中國大陸是最大排放國,一年排放超過143億公噸;美國約排放62.8億公噸, 歐盟約33億公噸;台灣則一年約排放2.6億公噸。可想而知,縱使個別國家的減碳績效非常好,並不足以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因為各國減碳成本高低不一,低成本國家容易減碳,高成本國家不容易減碳,因此放任各國自行減碳,同樣無法解決全球暖化問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了解到全球暖化是一個全球性議題,單獨管理個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難以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必須使用一個覆蓋全球的減碳工具,促進國際減排合作。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於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簽署《京都議定書》5(Kyoto Protocol) 。《京都議定書》依據歷史責任原則,在負擔「共同但有差異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 下, 將締約國區分為「附件一國家」(Annex I Countries,列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第一個附件),包括25個開發國及16個經濟轉型國(Economies in Transition),這些是負有減排責任國,平均減排5.2%(2008年至2012年平均排放量相較於1990年排放量)6 ; 其他沒有列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國家,稱為「非附件一國家」(Non Annex I Countries),不負擔減排責任。
由於附件一國家減排成本高,非附件一國家雖然減排成本低,但減排能力不足,因此《京都議定書》為促進全球減排合作,擴大減排能量,依據該公約第3.3條「締約國應考量以成本有效(Cost Effectiveness)政策措施」的母法要旨,制定3個彈性機制,稱為「京都機制」,包括聯合減量機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及國際排放交易機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IET),奠立全球碳權交易的法源,同時也觸動各國境內實施碳交易的思維。

在《京都議定書》的精心設計與制度安排下,3個彈性機制雖然目的都是促進國際減量合作,但各自負責差異性減量合作之功能(見左表1-1)。
聯合減量機制是針對附件一國家間的減量合作機制,創造的減碳成果稱為排放減量單位(Emissions Reduction Units, ERUs)。1單位排放減量單位代表1公噸CO2e。清潔發展機制則是針對附件一與非附件一國家間的減量合作機制,來自迴避(Avoidance)或減量(Reduction)計畫創造的減碳成果,稱為經驗證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 CERs),1單位經驗證減排量代表1公噸CO2e。來自移除(Removal)或封存(Sink / Sequestration)計畫創造的減碳成果,稱為移除單位(Removal Units, RMU)。
國際排放交易機制則是依據附件一國家的減排承諾或目標,核發排放配額,規範各國排放上限,稱為指定排放單位(Assigned Amount Units, AAUs)。由於1單位排放減量單位、經驗證減排量、移除單位及指定排放單位均代表1公噸CO2e,因此在《京都議定書》第17條規定,排放減量單位、經驗證減排量、指定排放單位及移除單位可在國際排放交易下,進行1:1的比例移轉(或交換),但是任何的移轉均需註冊,以利碳權追蹤管理,避免重複使用。
而任何一筆交易紀錄(交割與移轉)均透過在地的碳權交易所,將交易明細(交易數量、交易碳權型態及交易對象等資訊),與國家碳權管理帳戶連結,再串接至各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國家帳戶移轉與管理。
由於台灣不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沒有碳權帳戶可進行交割與移轉,因此若購買聯合國體制碳權,例如購買經驗證減排量僅能當下註銷(Cancellation),無法再進行移轉…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