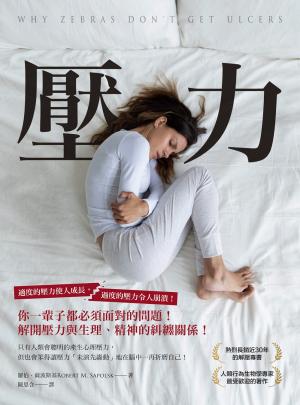如果你習慣這麼做,大約到了凌晨兩點半,當你冒著冷汗時,一個全新且具破壞性的連鎖想法必然會闖入你的腦袋。突然,你在各種擔心中,開始思索起身體側邊已經有好一陣子的不明確疼痛、耗竭的感覺,或是頻繁的頭痛。這個體認使你驚覺:我病了,病得快要死了!喔!為什麼我沒有意識到這些症狀?為什麼我要否認它?為什麼我沒去看醫師?
我總是在凌晨兩點半出現一個「腦腫瘤」!上面這些想法很能夠製造驚恐,因為可以把每個想到的不明確症狀都歸因於腦腫瘤,並且合理化每個驚慌。就是如此,你或許也會躺在那裡想著自己有癌症,或有潰瘍,或你剛剛中風了。
即使我不認識你,也能很有自信地預測,你不會躺在那裡想:「我就知道,我有痲瘋病!」對嗎?如果大便狂瀉,你不可能執著地認為自己感染了嚴重的痢疾。畢竟我們很少人會躺在那裡,深信自己身體裡的腸子或肝臟裡充滿了寄生蟲。
當然不會。我們的夜晚不會滿是對猩紅熱、瘧疾或鼠疫的擔心,霍亂並不在我們的社區中蔓延,河盲症、黑水熱、象皮病則是第三世界的異國風情,也很少有女性讀者會死於生產,至於閱讀著這一頁的營養不良讀者,就更少了。
多謝醫學和公共衛生的革命性進步,常見的疾病已經改變了,而且我們不必再夜不成眠地擔心感染性疾病,或是擔心營養不良或衛生問題造成的疾病。相較之下,想想美國在一九〇〇年的前幾大死因:肺炎、肺結核、流行性感冒(還有,如果你當時是年輕女性,並且有冒險傾向,生小孩也是其中之一)。你上次聽說一大群人死於流感,是什麼時候?那些流感在一九一八年殺死的人,比起最野蠻的衝突(也就是世界第一次大戰)還要多。
現今的疾病模式,對於我們的曾祖父母,或是對大部分的哺乳類來說,都是難以理解的。
簡單來說,我們得到的疾病和可能死亡的方式,跟大部分的祖先不一樣(或者跟現今住在地球上較弱勢地區的人類不同),以致在夜晚時總是充斥著對於其他種類疾病的擔心;我們現在活得夠好也夠久,足以讓身體慢慢壞掉。

▲一九一八年流感大流行。
我們已經認知到生理與情緒有非常複雜的糾結,我們的性格、感覺和想法,正以無盡的方式反映並影響著我們的身體狀況。這個認知的其中一個有趣發展,是了解到嚴重的情緒障礙可能會對我們產生有害的影響,用常見的話來說就是:「壓力會使我們生病。」醫學上一個重要的改變,就是認知到許多慢性累積、具傷害性的疾病,可能是壓力所造成的,或是壓力會使之嚴重惡化。
就某些方面來說,這已經不是新聞了。數個世紀之前,敏感的醫師們直覺地意識到,每個人對疾病的反應有個別差異,兩個有相同疾病的人,各自的病程發展卻相當不同,並且以模糊又主觀的方式反應出個別的人格特質。或者,一位醫師可能感覺到,某些類型的人比較容易得到某類疾病。但自從二十世紀以來,這些模糊的臨床觀點加入了嚴謹的科學,使得研究身體如何回應壓力事件的「壓力生理學」,成了一門真正的學問。於是,現在有非常多生理、生化、分子方面的資訊,解釋了生活中各種無形的情況如何影響我們有形的身體。這些無形的事物,包括情緒痛苦、心理特質、社會地位,以及社會如何對待在那個位置的人,而它們可以影響健康問題,像是膽固醇會塞滿血管還是安全地從循環中被清除;或脂肪細胞是否不受胰島素控制,導致我們有糖尿病;或大腦裡的神經元是否能夠撐過心臟停止而導致缺氧的那五分鐘。
這本書是關於壓力、壓力相關的疾病,以及應對壓力機制的入門書。為什麼我們的身體能夠調適一些有壓力的緊急狀況,但有些壓力卻會使我們生病?為什麼有些人特別容易得到壓力相關的疾病,這又與性格有什麼關係?為何單純心理層面的問題就能使我們生病?壓力與我們多容易得到憂鬱症、多快速老化、記憶力好不好,有什麼關係?我們的社會階層,又與壓力相關疾病的模式有什麼關係?最後,我們如何可以更有效地應對周圍充滿壓力的世界?
壓力與身體的恆定性
最好的開始方式,或許是在腦袋裡列出一串我們會覺得有壓力的狀況清單。你應該會立刻想出一些明顯的例子,如路況、截止日、家庭關係、擔憂金錢,但如果我說:「這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方式,現在試著像斑馬那樣思考。」突然間,有些新的東西會跳上清單的前幾名,如身體嚴重受傷、狩獵者、飢餓。當我們需要被提醒換個角度去想時,正顯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你我比斑馬更容易得到潰瘍。
對動物而言,比如斑馬,生活中第一類難受的事情,是緊急的身體危機。如果你是那隻斑馬,一隻獅子剛剛跳出來想撕裂你的肚子,你逃走了,接著花一個小時逃避還在糾纏你的獅子。或者,同樣很有壓力的,你是那隻獅子,非常飢餓,你最好用最快的速度衝過大草原抓住什麼來吃,否則你就無法活下去。這些是極度有壓力的事件,而且需要立即的生理適應才能存活,而身體的反應,會非常傑出地適應並處理這些緊急狀況。
一個有機體也可能被長期的身體挑戰所糾纏,這是第二類的難受。蝗蟲吃了作物,接下來六個月,你必須每天走上十幾公里去取得足夠的食物。乾旱、饑荒、寄生蟲,那些不愉快的狀況不是常會有的經驗,卻是未西化的人類和大多數哺乳類生活的中心事件。而對於這些持續性的災難,身體的壓力反應還算可以應付。

▲羅伯特.朗溝(Robert Longo),紙上的無名作品,一九八一。(兩個雅痞為了餐廳最後一份雙倍拿鐵而打架?)
我們能夠光靠連結想法,就體驗強烈的情緒(激發我們的身體進入隨之而來的騷亂)。【1】兩個人可以面對面坐著進行冠軍棋賽時,進行不比偶爾移動小木塊更耗體力的事情,卻非常消耗情緒,而且新陳代謝的需求可能接近運動員在競爭性比賽高峰時的狀況。【2】或者,一個人只不過簽一張紙就感到興奮,因為他花了好幾個月密謀操弄,然後在剛剛簽字開除了一個厭惡的敵手,他的生理反應可能會驚人地像是大草原的狒狒,剛剛把競爭對手的肺打爆、把臉割爛。如果一個人為了某些情緒問題而使內臟糾結於焦慮、憤怒和緊張好幾個月,就非常可能導致生病。
這是這本書的重點:如果你是逃命的斑馬,或是衝刺覓食的獅子,你的生理反應會很好地適應去處理這類短期生理緊急事件。對地球上絕大多數的猛獸來說,壓力來自於短期的危機,然後要不是那個危機沒了,就是你自己沒了。而當我們枯坐著擔心有壓力的事情時,也同樣開啟了相同的生理反應,只是當它們被持續性地激發時,就可能是個災難。大量的證據顯示,壓力相關疾病大多來自於我們太常啟動那些應該用來回應急性身體緊急事件的生理系統,而且一打開它就是好幾個月,因為我們總是擔心著房貸、人際關係和工作。
我們的壓力和斑馬的壓力之間的差別,使我們開始深思一些定義。一開始,我必須提起一個在中學生物課上可能折磨過你的概念,也許你從那時起就希望不必再想到它,也就是「恆定性」,像是身體有需要氧氣的理想程度、理想的酸鹼度、理想的體溫等。這些不同的變項被維持在恆定的平衡裡,是一種所有的生理狀態都維持在最佳程度的情況,而大腦被認為已經進化到要維持情況恆定不變的狀態。
這讓我們產出一些簡單的初期工作定義,而它們對斑馬或獅子而言是足夠的。此定義為:壓力源是來自外在世界,而且把你的恆定性打破的東西;壓力反應則是你身體試圖重建恆定性的作為。
但是,當我們考慮到經常讓自己以及人類擔心到生病的情況時,我們不能把壓力源僅僅解讀為「打破你恆定性的東西」。壓力源也可以是「對於即將發生什麼事的預期」。有時候我們夠聰明,可以看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然後僅僅根據預期,就能開啟宛如事情真的發生一樣的強烈壓力反應。
某些層面的預期性壓力並不僅限於人類,無論你是在荒涼地鐵中被一群流氓包圍的人,還是與獅子面對面的斑馬,你的心臟都會狂跳,即使還沒有發生什麼身體傷害。但是,我們不是那種認知層面較簡單的物種,而是只要想著很久以後可能破壞我們恆定性的壓力源,就會開啟壓力反應。例如,非洲農人看著一大群蝗蟲降臨在他的作物上時,即使他已經吃了足夠的早餐,也沒有因為挨餓而恆定性失衡,但是他仍會經歷壓力反應。斑馬和獅子會看到下一分鐘的麻煩,並在預期中啟動壓力反應,但是牠們無法對遙遠的未來事件感到壓力。
有時候,人類會為了斑馬或獅子覺得完全沒道理的事情而感到壓力,如為了房貸、稅單、對大眾演講而焦慮,或是害怕求職面試要說什麼、無可避免的死亡等等,這些都不是哺乳類的通性。人類經驗裡充斥著心理性的壓力源,與飢餓、受傷、失血、極端氣溫的生理世界大為不同。
當我們因為害怕什麼會成真而啟動壓力反應時,就是在讓自己這個認知技巧允許我們提早啟動防禦,而這些預期性的防衛可以有相當的保護力,此時的壓力反應大多與「準備」有關。但是,當我們進入了生理性的混亂,並且沒道理地啟動壓力反應,或是為了無能為力的事情而啟動它,就是一種「焦慮」、「神經質」、「疑神疑鬼」或「不必要的敵意」。
因此,壓力反應不只能在生理或心理的攻擊中啟動,也能在預期心理中啟動。生理系統不只能被各種身體災難所啟動,也能在光想著那些事情時就被啟動,這種壓力反應的廣泛性是令人驚訝的。這種廣泛性最早在數十年前即受到壓力生理學的教父之一——漢斯.塞利(Hans Selye)所重視。
開個玩笑:壓力生理學能成為一門學問,是因為漢斯.塞利雖然非常有洞見,卻是個非常不會處理實驗室老鼠的科學家…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