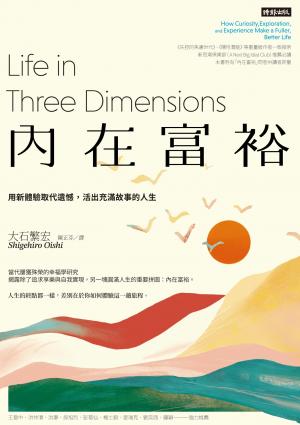如果我留,麻煩只會翻倍。
──衝擊合唱團(The Clash)

1. 安適的人生
阿義出生在日本九州的小山村,一個以生產綠茶和蜜柑知名的地方。阿義就像他的父親、祖父和在他之前的所有男性祖先,一輩子住在那裡,種稻米和茶為生,他才上了一年的農業高校就選擇輟學務農,走上這條老路。二十七歲那年,阿義娶了鄰鎮的女孩,有了三個孩子,他參加街坊組成的壘球隊,一直打到五十幾歲,每年會跟鄰居結伴到各地的溫泉暢遊。至今他依舊住在這座小鎮,還是同一位妻子,親近的友人還是那幾個從小學就認識的,阿義選擇遵循先人的足跡,他與祖先不僅血脈相連,就連職業、住所、期待和生活方式都緊緊相繫。
阿義是我父親,而我是他遠在天邊的兒子。我剛過完十八歲生日後,花了整整十八天才從我住的小山村來到東京上大學。大四那年,我獲得國際扶輪社(Rotary International)的獎學金,到緬因州留學。留學的課程開始前,我先到紐約市的史泰登島(Staten Island)去參加暑期英語課程,當時我剛和東京的女友分手,對談戀愛心灰意冷,只想把英文讀好,但我認識了一位韓國學生並墜入愛河,當時她即將前往波士頓讀研究所,我則是即將去緬因州的劉易斯頓(Lewiston)留學一年。一九九一至九二年的那個學年間,我每週末搭灰狗巴士去波士頓看她,到了五月,我必須回東京,儘管我在留學前的生涯規劃是去日本的文部省工作,全然沒有打算在美國念研究所,但那時我已下定決心要回美國。一九九三年六月畢業後,我離開日本,從此不再回去,之後流轉於紐約市、伊利諾州香檳市(Champaign)、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市(Minneapolis)、維吉尼亞州夏洛特鎮(Charlottesville)等地,最後在芝加哥落腳。在這過程中,我娶了在史泰登島認識的韓國女孩,我們的兩個孩子分別出生在兩個不同的城市。我已經多年沒有和任何一位兒時的友人見面。
離開家鄉三十年後,隨著年紀增長,加上試著維持家族的情感聯繫,我經常納悶著我的人生怎麼會與父親的人生差距如此之大,我想知道為何他有機會卻不離開家鄉,相反地,我也想知道自己為何如此漂泊。
父親的人生安定、熟悉且舒適。春季的年度賞櫻會,夏季的盆踴祭典,秋季的賞楓之旅,冬季的溫泉。安適美好的人生。相反地,我的人生一點也不安定、一點也不熟悉,承受著更多壓力,來自授課、批改成績和寫作截止日期,當中混雜著無數次被拒之門外的經驗(例如:申請經費、論文、書籍企劃提案、應徵工作等)。雖然我多半時間熱愛著自己的工作,但有時我真心忌妒父親那單純、怡然自得的生活,希望每個禮拜能有個晚上跟老朋友喝個小酒,回憶學生時代,聊聊農事,但老實說,我知道自己不可能過那樣的生活,因為我極度渴望見識外面的世界,渴望到無法遵循祖先一路走來的一成不變的生活。
2. 幸福、意義及其他
我回想在高中畢業時,面對衝擊合唱團(The Clash)那句不朽歌詞的提問:「我該留還是該走」,那時答案很簡單,走就對了。但隨著年紀增長,這問題也愈來愈難回答,幾十年來,它已經成為我個人生活和學術研究的核心。我猜想大部分的讀者也曾經問過自己相同的問題,不只一、兩次,而是很多很多次。你們之中的一些人或許就像我父親那樣,忠誠、謹慎且念舊,將安定列為人生的優先;有些人或許比較像我,對外界的變化敏感、異想天開、愛冒險,擁抱大膽探險的人生。當然,安定和變動的人生;單純與高潮迭起的人生;舒適和挑戰的人生;傳統與非傳統的人生,這之間存在著利弊得失,但是,哪一種才能讓我們更接近「美好」的人生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會汲取我數十年來的心理科學研究,輔以現有文學、電影、哲學著作中的案例資料,但我們首先要問的是,究竟什麼是美好的人生?
當《金翅雀》(The Goldfinch)的作者唐娜.塔特(Donna Tartt)被問到她在這本小說中想探討什麼問題時,她回答:「什麼是美好的人生……是讓自己感到幸福?是屬於個人的幸福?還是哪怕犧牲自己的幸福也要讓別人幸福?」塔特的提問值得深思。我們是否應該努力追求幸福?還是先努力使他人幸福,然後才想到自己?
首先,什麼是個人的幸福?什麼使你幸福?是能夠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還是追求並完成事業目標?又或是到海邊玩耍或是做spa?我在人生中曾經做過很多自私的決定,包括在我兒子們還就讀初高中時搬到紐約,到一所聲譽卓著的學校工作,儘管兒子不想離開家鄉和他們的朋友,我還是選擇使個人的幸福極大化,而到頭來,我並不覺得自己更幸福。相反地,我父親則決定留在家鄉,或許是為了使我母親和其他人幸福而犧牲了他自己。如果搬到縣內另一個熱鬧的城市,他賺的錢大概會多很多。諷刺的是多年後,他對當初決定的滿意程度似乎高於我,這聽起來像是什麼中國諺語的故事,卻闡釋了一個更大的真理:心理學的研究顯示,試圖使他人幸福將使你幸福,而試圖使自己幸福,卻往往無法如願。心理學家發現,利他目標的花費、寫感謝信、懷抱知足心態(也就是安於所有),都能提升幸福的程度,父親如此幸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調整自己的期望,珍惜在田裡的每一天,享受老伴在身邊的小確幸。
父親的美好人生,關鍵或許在他決定將他人(包括我母親和家族傳統)的需求置於自己的需求之上,話雖如此,以自我犧牲與美德為主軸的人生──或許可以被稱為「有意義的人生」──是無怨無悔的人生嗎?人會為最近做過的事後悔,後悔說了不該說的話或是做了不該做的事,然而從長遠來說,人會為自己沒有做的事後悔,像是沒有說出「我愛你」,或沒有回學校繼續進修,有些人過著自我犧牲與美德的人生,卻錯過種種機會,最終招致更多的遺憾和悔恨;自我犧牲確實令人敬佩,但是把自我犧牲擺第一位,可能會使你看不見自己的渴望和理想,直到感覺人生不再真實。法國哲學家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會將之稱為「自欺」(bad faith)的人生,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說《秀拉》(Sula)中就出現了這樣的例子,書中的妮爾.萊特(Nel Wright)擱置了兒時的冒險」夢想,按著家人的期待扮演完美妻子與母親的角色。
光譜的另一端,我們可以找到神經學家兼作家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他是機車幫會「地獄天使」(Hells Angels)的活躍分子,是一名健美先生,吸食過LSD(一種會產生幻覺的迷幻藥物),之後才展開寫作生涯。他在大學時期與憂鬱症對抗;親生母親告訴他,當她得知他是同志,恨不得從沒生下過他;他的成年生活中有三十五年抱持獨身主義。儘管有過艱困歲月,他的生命中充滿冒險與好奇、對專業領域界線的挑戰,以及深度體驗和豐富的情感,換言之,那是本真的人生,是沙特讚許的那種人生。
3. 什麼是內在富裕的人生?
奧利佛.薩克斯的故事呈現出一種困境,他患有憂鬱症且長期處在內心掙扎的狀態,但他還是持續探索新的世界,他在二○一五年出版了自傳《勇往直前》(On the Move:A Life),書名可說恰如其分。個人的幸福與滿足,或者自我犧牲與美德,都無法貼切說明薩克斯人生為何如此讓人敬佩,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說法,我和我的學生們決定稱之為「內在富裕的人生」。內在富裕的人生充滿變化多端的、不平凡的、有趣的體驗,能改變一個人的觀點;是曲折迴旋、高潮迭起、多采多姿的人生。不是直白易懂的,而是多樣與複雜的人生。是有許多停頓、迂迴和轉捩點的人生,感覺就像是漫長蜿蜒的健行,而不是在相同的賽道上一圈圈地跑。黑巧克力相對甜巧克力,是個不錯的類比,當你吃下一片細緻的黑巧克力時,會立刻察覺到它有別於一般甜膩的巧克力,它苦中帶甜,甚至帶點鹹,使你驚喜,味覺的強度更高、更複雜且更具深度,換言之,它是豐富的。同樣道理,內在富裕的經驗有別於一般經驗,有種超乎意料且強大的力量,具有多樣的特質,而不是非黑即白。經過時間累積,內在富裕的經驗形成了內在富裕的人生,也是風味繁複鮮明的人生。內在富裕的人生,也就是擁有豐富體驗的人生。
但是,我們為何需要這個新的詞彙呢?要解釋這個疑問,接下來讓我們稍微離題,進入心理學領域中關於美好人生的研究史,我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階段一:幸福研究的興起
我的研究所指導教授艾德.迪安納(Ed Diener),是最早研究幸福的學者之一,他於一九八四年出版一篇題名為〈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的論文。艾德與藍迪.拉森(Randy Larsen)和鮑勃.伊蒙斯(Bob Emmons)等他的學生們,在一九八○年代又出版一系列關於主觀福祉的論文,正式成立了心理學中有關幸福的科學研究。之後,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根據幸福以及希望、樂觀和心流等相關主題進行的研究,更為大眾所知的正向心理學建立起基礎。
.階段二:意義式幸福感的挑戰
到了一九八九年,卡洛.雷夫(Carol Ryff)出版一篇題為〈幸福是王道,真的嗎?〉(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的論文,提出美好人生的另類模型,聚焦在自主、自我接納、目的、正向關係、環境掌控以及個人成長。艾德.德西(Ed Deci)和李察.萊恩(Richard Ryan)的自決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以及雷夫對美好人生的觀點,被統稱為「意義取向」(eudaimonic approach)──亦即有意義的人生;與之對比的是艾德.迪安納、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丹.吉伯特(Dan Gilbert)、索妮亞‧柳波莫斯基(Sonja Lyubomirsky)等人,他們對美好人生的觀點被統稱為「享樂取向」(hedonic approach),亦即幸福人生。
.階段三:論戰
過去二十年間,福祉研究學者對享樂式和意義式幸福感的福祉究竟何者重要持續辯論著。舉例來說,自認生活順遂的人,往往也會說自己是幸福的,但未必會說自己的人生有意義。上班族在休息時比工作時快樂,但是在工作時比在休息時更投入。一些研究學者甚至宣稱,他們已經發現享樂式和意義式的福祉之間存在不同的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模式,認為我們從基因本身的表現方式就有所不同;但亦有研究學者發現,幾乎所有表示自己幸福的人,也往往會表示自己的人生是有意義的,反之亦然。由於享樂式與意義式福祉如此大幅重疊,一些研究學者便主張兩者實質上是同一回事;還有些人則主張,幸福和意義兩者對人生都是如此重要,根本無須爭辯何者為重。
4. 第三維度的利用
研究福祉的學者們,針對幸福與意義何者重要爭辯不休,各自主張一個比另一個重要,我個人的看法是幸福和意義兩者都重要,儘管如此,兩者卻也都無法充分詮釋薩克斯那種冒險、非傳統且高潮迭起的人生。換言之,心理學家從沒有充足的詞彙來形容這樣的人生。某方面來說,「幸福」相對於「意義」的爭論,和心理學領域的另一場辯論相當:何者為預測智力最重要的因素,先天條件(基因)還是後天教養(環境)?到頭來,結論是先天後天都重要。後來卡洛.德威克(Carol Dweck)提出的第三種想法為人們普遍接受,那就是成長心態。她證明人對智力的觀點──明確地說,人是否相信智力可以進步──對預測智力和人類表現也具備重要性。
有天晚餐時,妻子說起客廳窗戶上的窗繩斷了,問我可不可以修理(我們的家是一幢十九世紀末維多利亞式的房子,有著原始的雙懸窗,要靠窗繩操作的那種)我回答:「應該要請人來做吧,我的手不夠巧。」這時我正在讀中學的次子立刻說:「爸,你這是定型心態(fixed mindset),你可以進步的!」原來他在學校才剛學到德威克的成長心態。兒子的建議成為我修理窗戶的動力,想要成為雙手更巧的人。這個小例子說明,成長心態這樣的概念能如何拓寬我們對於自我、他人與世界的想法。一如成長心態揭示了人類智力與能力的新維度,我希望內在富裕也能展現美好人生的新維度。
那麼,內在富裕,跟幸福和意義有什麼不同?本書的主要篇幅會詳細回答這個問題(請見表一的簡略摘要),如果要簡短說明,幸福是主觀感受,幸福的生起和消滅顯示一個人當時的人生狀態,有點像是氣球,在適合的風與氣壓下,氣球就能高飛,在空中順利航行,人生一帆風順。但是當天氣不佳,氣球會洩氣並掉落地面,動彈不得,人生卡卡。換種方式說,幸福就像棒球打擊率,總會有高有低,但最重要的是擊球的頻率,就打擊率來說,一支內野安打和一支全壘打的價值是相同的,你的目標應該是盡可能打出安打;換言之,相較於偶爾大幅度加薪,小而愉悅的經常性社交互動,更能快速累積成為長期的幸福。
難就難在幸福就像打擊率,會隨時間改變,這一季打得很好,下一季未必如此,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宗教經驗之種種》(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提出:「首先,世界上的成功經驗如此靠不住,如何成為穩定的基準呢?鎖鏈的牢固與否由它最弱的環節所決定,而人生說到底就是條鎖鏈,在最健康、最富有的生存方式中,穿插了多少疾病、危險與災難的環節?」所以說,幸福是脆弱的。
另一方面,人生的意義,終歸在於人生是否存有「重點」。當你致力於改變世界,人生自然有了重點,你會看到辛勞的成果,也是你留給後人的遺澤,你的存在有了理由。但是當你的努力沒有顯著效果,就比較難看到人生的重點為何,蘇格蘭創作歌手路易斯.卡柏狄(Lewis Capaldi)在其歌曲《無謂》(Pointless)中唱到:「我所追逐的一切夢想……少了你都將是無謂。」想像他跟這位女性分手會是怎樣。他的付出將付諸東流,人生也失去了重點。
托爾斯泰是幸福且創作力豐沛的。但是,在沒有任何明顯的失落下,他在大約五十歲時(《戰爭與和平》出版的數年後)突然出現存在危機。「我有個好妻子且我們彼此相愛,我的子女們都是好孩子,我坐擁一大筆毫不費力便能持續增長的財產,我受到親朋好友比以往更高的敬重,我收到陌生人滿滿的讚美,不誇張地說,我的聲名遠播……但我在人生的一切所作所為中,卻找不出合理的意義。」所以說,意義是動盪不定的。
5. 本書是關於……
內在富裕有別於幸福和意義,它非關人生未來的走向,也非關人生重點的整體感受,而是一種體驗,更精確地說,是經驗的「累積成果」。物質的富裕可以用金錢量化──你的錢愈多,物質上愈富裕──同樣道理,內在的富裕可以用經驗量化,擁有愈多有趣的經驗和故事,內在也愈富裕;就好比你可以累積財富成為物質上富裕,你也可以累積經驗而成為內在富裕的人。如果幸福像打擊率會隨每場比賽改變,內在富裕則更像是職業生涯的全壘打紀錄,是累加的…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