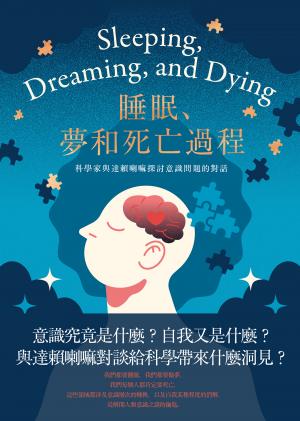自我概念的歷史
從以往同達賴喇嘛尊者對話的心智與生命研討會中,我們得出一個經驗:有一位專業的哲學家來參與討論會上科學議題是非常有益的。這樣做的重要原因是,西藏傳統極為看重哲學領域的思考和訓練,西方哲學家的參與往往能夠提供很有價值的聯繫橋梁,或另一種對西藏傳統來說更清晰、更貼切的表述。針對這次研討會的議題,查爾斯.泰勒作為知名的哲學家和作家,是擔當此任的理想人選。在他新近出版的著作《自我之來源》中,他生動而深刻地描述了我們西方人怎樣思考我們稱為「自我」(self)之物。1他開門見山,準確地開始談論這個問題。
「我想談一談西方人理解自我的幾個最重要方面。為此,我要描繪一關於這個概念的歷史的大致發展。我想應該從『自我』這個表述本身開始。在我們的歷史中,說『我是一個自我』是件相當新近的事情,是在過去一兩百年裡才出現的。在此之前,我們從來不把反身代詞『自我』和一個定冠詞或不定冠詞(如the或a)放在一起。古希臘人、古羅馬人以及中世紀的人,從不把這個詞作為一種描述性的表達。我們今天可以說,在房間裡有三十個『自我』,而我們的祖先是不會這樣說的。他們或許會說房間裡有三十個『靈魂』(soul),或者別的什麼描述,但是他們不會用『自我』這個詞。我認為這反映了我們對人的主體性理解中一些非常深刻、深植於西方文化的內容。」
「在過去,人們不加區別地使用『我自己』(myself)或「我」(I)這樣的詞,但是『自我』這個詞現在被用來描述一個人是什麼。我永遠不會用『我』來描述自己。我只是用這個『我』字來指稱自己。我會說:『我是什麼?我是一個人;我來自加拿大。』我用這樣的方式來描述自己,但是從20世紀開始我可能會說『我是一個自我』。我認為這個很重要,原因在於我們選擇這樣的描述性表達反映了我們認為精神方面或道德方面對人類很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祖先把我們稱之為『靈魂』,因為這對他們來說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很重要。」
「為什麼人們變得對這樣的說法感到不舒服而轉向使用『自我』這個說法?部分原因是他們發現,在把我們描述為『自我』的時候,有一種精神上很重要的東西。我們擁有某種能力來反思自己,來對我們自己做一些事情,這成為西方人文生活的道德和精神核心。歷史上,我們有時候稱自己為『靈魂』或『智慧生物』,因為這些概念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我們稱自己為『自我』,因為有兩種反思自我的方式成為我們文化的核心觀念,它們在現代西方生活中形成了一種張力,這兩種方式就是自我控制和自我探索。」
「我們先來看自我控制。公元前4世紀的偉大哲學家柏拉圖談到過自我主宰。柏拉圖的意思是,人的理性在控制著人的欲望。如果人的欲望控制了人,那麼人就不是自己的主宰。」
「非常智慧!」達賴喇嘛插話。
「有意思的是,柏拉圖所說的自我控制跟現代世界的意思很不相同。對柏拉圖來說,理性是人類把握宇宙秩序的能力,他稱之為『觀念』秩序,這些秩序給了宇宙以形狀。讓理性掌握人的靈魂,就像讓宇宙秩序掌握人的靈魂是一樣的。如果我看到了事物的秩序,我的靈魂就因為熱愛這種秩序而進入了這種秩序。所以,那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被我自己所控制,而是被宇宙秩序所控制。人並不被鼓勵去向內反省自己靈魂的內容,而是被鼓勵去向外掌握事物的秩序。」
「在公元4世紀,基督教的聖奧古斯丁深刻地改變了這一觀念。他受到柏拉圖的影響,但是他的看法很不一樣。他的觀點是,我們可以面向自己的內心,檢查我們內心有些什麼,通過這樣做來接近上帝。我們發現,在事物的核心問題上,我們依賴於上帝的力量,所以我們通過審察自己而找到上帝的力量。」
「於是我們有了這樣兩個精神層面的方向:一個是柏拉圖的,是外向的;另一個是奧古斯丁的,是內向的,不過目的仍然是要達到我們自身之外的某種力量,也就是上帝。第三個變化來自於現代西方世界。以17世紀哲學家笛卡爾為例。笛卡爾相信上帝,他自視為奧古斯丁的追隨者,但是他對自我控制這個觀念的理解完全不一樣:我作為一個代理而做到的工具性控制,可以掌控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我在和我自己的關係中,就像我在和某種工具的關係一樣,我可以用於任何我想要的目的。笛卡爾重新解釋了人類生活,我們把自己看成工具。我們把我們的肉體存在看成是我們可以使用的機器,這種思想出現在產生了對世界的機械論解釋的偉大時代。」
「現代的自我控制思想和柏拉圖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宇宙秩序已經不再重要,已經與我們無關了。我們不再處於宇宙秩序的控制之下。我現在甚至不再通過內省來超越自己而面向上帝;我有一種自身存在的能力來安排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用理性作為一種工具來控制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讓自己的思想以正確的方式步驟運作,就像一種我能夠以某種方式加以控制的客觀領域,這些對我來說變得非常重要。這已經成為西方生活處於絕對核心的思想。這是我們將自己看成『自我』的一種方式,因為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的感情或思想的具體內容,而是我們能夠通過思考來控制它。」
心智與生命研討會的習慣做法是,在講解的過程中,演講者要對達賴喇嘛提出的問題做出解釋。事實上,通過這些問題,讀者可以清楚認識到西藏傳統和西方傳統之間的鴻溝。此時,尊者禮貌地問道:「你是不是說,這個作為控制者的自我跟受制的身體與心智(body and mind)有同樣的本質?還是說,它的本質不同於身體與心智?」
「對笛卡爾來說,這是相同的,」查爾斯回答說,「但是自我看起來是不同的,因為它本身沒有任何特定的內容。它只是一種控制思想或身體的能力。」
自我探索和現代性
然後討論轉向自我探索。「在笛卡爾發展出這些思想的同時,西方出現了人類另外一個重要的能力:自我探索。這是從奧古斯丁激發的基督教靈性盛行之中產生的,它引導人們面向自我審察,考查自己的靈魂和生命。自我審察的發展也超出了起初的基督教形式,在後來的兩百年中成為非常強大的思想,並且已經成為當代西方世界的一個基本理念,即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原初的作為一個人的方式。」
「古代就有自我探索的實踐,但總是始於我們已經瞭知人類的本質這樣一個假設,我們的任務是在自己的內心裡找到我們已知為真實存在的東西。在過去的兩百年裡,我們的假設是,我們大致知道人類本質是什麼,但是因為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原初作為人的方式,所以我們要通過自我探索來把這個本質從我們內心深處發掘出來。這樣做打開了人類能力的一個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全新領域。你怎樣探索自己?你去尋找那些尚未說出、尚未表達的東西,然後找出一種方法來表達。自我表達變得至關緊要。」
「你怎樣找到自我表達的語言?過去兩百年裡,西方世界認為,人們可以在藝術中找到最好的自我表達語言,無論是詩、視覺藝術,還是音樂。現代西方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認為藝術幾乎具有宗教般的意義。特別是那些沒有傳統宗教意識的人,往往對藝術抱著深深的尊崇。西方的一些偉大表演者光環繞身,廣富盛名,受人崇拜,被人追捧,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未有過的。」
「於是我們有了這樣兩種和自我有關的做法:自我控制和自我探索。因為二者都是至關緊要的,我們開始把自己看成是『自我』,自稱為一個『自我』,而不再去想它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兩種做法都屬於同一個文化,但是它們之間也有深刻的衝突,我們的文明一直在為這種衝突而糾結。你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衝突。」
「今天你在西方可以看到這種衝突,對世界和自身持有非常嚴格、狹窄、技術性思維的人,和那些以生態健康及開放的名義反對他們的人之間就有這樣的衝突,因為自我控制的技術性立場同時也關閉了自我探索。」
「你也可以從對待語言的態度上看出來。一邊認為語言是一種由心智控制的單純工具,另一邊則認為語言將引向最豐富的人性發現,語言是人所存在的空間,語言將打開人類本質的最深的祕密。」
「將自我控制和自我探索帶到一起的是它們的共同來源:聚焦於一種自我閉合形式的人類概念。柏拉圖不能理解處於和宇宙的關係之外的人類,奧古斯丁無法理解處於和上帝的關係之外的人類。可是現在我們有了一幅人類的圖景,在這幅圖景中,你可以相信上帝,你也可以去同宇宙發生聯繫,於此同時,你也可以通過自我控制和自我探索的能力,以一種自我閉合的方式來理解人類。這也意味著,在西方的道德和政治生活中,最核心的價值或許是自由,是控制自己的自由,是理解自己是誰,成為『真我』的自由。」
達賴喇嘛再次要求解釋一個關鍵問題:「在這裡面是不是有這樣一種預設,自我控制必然意味著一個自身存在或自治的自我,而自我探索意味著對此有所懷疑?」查爾斯回答說,並不一定如此,自我探索也肯定自我,但是創造了一種可能性,即探索可以超越自我。自我控制的立場則毋庸置疑地認為有一個控制者的存在,例如笛卡爾哲學非常著名的觀點是從如下確定性出發:我,我自己,是存在的。對世界的科學理解的整個大厦,就建立在這種確定性之上。」…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