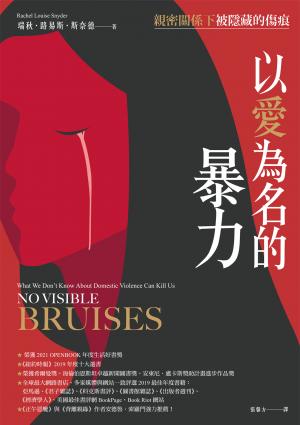保羅.孟森的房子採開放式格局,客廳可通到飯廳,飯廳可通到廚房。他跟我說,以前孫子和孫女會在屋裡跑來跑去。他指的是克莉絲蒂與凱爾。他們來拜訪外公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像兩個小瘋子一樣到處狂奔。克莉絲蒂與凱爾是洛基與蜜雪兒的孩子。
保羅來自北達科州(North Dakota)邁諾特(Minot),因為工作的關係來到了蒙大拿。他父親很久以前就過世了,繼父基爾(Gil)是巡迴馬戲團「倫德的兒童天地」(Lunder’s Kiddyland)的老闆,在那之前是位農夫。保羅稱他是「只要有錢啥都好談的男人」。蜜雪兒深愛她的祖父母。
「很多時候人們都說女孩子會愛上跟自己的父親相像的男人,」保羅說,「但我在洛基身上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也許是洛基的活力吸引了蜜雪兒,保羅說。抑或是他們認識的時候,蜜雪兒還是少女,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二十四歲年輕許多的洛基已經接觸過成人世界,讓她覺得很新鮮。他成天在家飲酒作樂,沒有人管。假使蜜雪兒沒有在十四歲懷孕、在十五歲生下克莉絲蒂,假使他年紀沒有大她這麼多,他們的戀情很有可能會像多數少男少女的羅曼史一樣,一開始愛得轟轟烈烈,最後無疾而終,然後各自遇到新的對象。「我覺得他那時候是年紀到了,想要安定下來,」保羅說,「成家立業之類的。」
保羅說,他與蜜雪兒幾乎每天都一起吃午餐。他工作的地點離她家很近,午休時間會過去找她,而他認為洛基應該從來都不知道。「我會帶午餐過去,蜜雪兒打開電視轉到傑瑞.斯布林格秀(The Jerry Springer Show),然後我們坐在沙發上一起看節目。」他說,「我跟她比其他女兒親近,不知道為什麼。她也跟我比較好。」
之後,保羅伸手拿起一疊用項膠帶捆起來的自錄DVD。他說這些是要給我的,是他在我來訪之前拷貝的家庭影片。以前洛基會用相機錄下任何活動,年復一年,尤其是全家幾乎每個週末都會一起露營的旅行。這些影片拍的不是特殊節日、假日和生日之類的內容,而大多是蜜雪兒、克莉絲蒂與凱爾的日常生活。保羅說他全都看過,而且不只一遍。他是為了尋找線索,尋找任何可能透露洛基有暴力傾向的蛛絲馬跡,但一無所獲。他們看起來就跟任何穩定、美滿的家庭 一樣。影片中有三歲大的克莉絲蒂坐在沙發上看卡通的畫面,也錄下凱爾手拿兒童釣竿在溪邊釣魚的過程。好幾部影片中,蜜雪兒在床上熟睡時被鏡頭後的丈夫輕輕喚醒。保羅說,一點線索也沒有。我自己則是過了好幾年才忍心看這些影片。
保羅的前妻莎莉.賈斯塔德跟保羅一樣對洛基知之甚少,即便是他還在世的那些年。他們兩個年紀較大的女兒艾莉莎與蜜雪兒在十五和十四歲時開始與保羅同住。莎莉與保羅幾年前離婚了,那時蜜雪兒八歲,大部分時間女兒們都跟莎莉一起生活。但進入青春期後,她們發現,在父親這裡可以擁有與母親同住所沒有的自由。
有時莎莉會致電保羅關心女兒的行蹤,但他完全不知道她們去了哪裡,有時就隨口編說「她們去誰誰誰家」,然後莎莉開車經過時會發現她們根本不在那裡。有次保羅給她一個住址,結果那裡是收容來自派恩山(Pine Hills)的男孩、幫助他們更生的中途之家。那些男孩有藥物上癮或行為的問題,年紀太輕無法坐牢,但待在家裡又太過危險——對自己與別人而言皆是。派恩山是專門收容不良少年的照護機構。莎莉很熟悉這個地方,因為她在蒙大拿州從事職業輔導,專門協助無行為能力的人們找工作。
那天晚上,她怒氣沖沖地把車子停在中途之家門口,焦急尋找當時才十三、四歲的蜜雪兒。應門的男人說蜜雪兒有來過,但之後又跟一個名叫科迪(Cody)的男孩離開了。莎莉氣炸了。她跟那個男人說,我不會讓女兒再來這裡,永遠不會。三個小時後,蜜雪兒出現了。
另一次,莎莉開車到保羅家門前,看到一台敞篷車停在前面,一台她沒看過的車。她敲門,無人應答,但她看見屋內有人影,於是又大力敲了幾下。還是無人回應。她離開了一會兒回來再試一次,還是一樣。她透過門縫大喊,如果不開門,她就報警。結果奏效了。蜜雪兒開了門。只見屋內有個年輕人頭髮蓬亂,身穿牛仔褲和T恤。他有著結實的下巴,彷彿無時無刻都在緊咬牙根。嘴唇豐厚,兩頰有一些痘疤。這是莎莉第一次見到洛基。他似乎很害羞,不敢直視她。她對他說,他不能在這裡,因為蜜雪兒的爸爸不在家。他支吾地說自己正要離開。
後來,莎莉告訴保羅,那個男生對蜜雪兒來說年紀太大了。她不知道他幾歲,但年紀大到有一台車的男生對十四歲的蜜雪兒來說太老了。她以為之後她與保羅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以為洛基會退出蜜雪兒的生活。她從沒想過蜜雪兒會不聽話;在莎莉心中,蜜雪兒依然是小女孩,依然是那個會自動做家事與從不翹課的乖女兒。蜜雪兒一直都不是叛逆的女孩。長大後(比保羅與莎莉想的快了許多),她變了。她直接變成了大人,錯過了一大半的青澀時期。
洛基身材精瘦,約一百六十五公分高,很容易緊張,精力充沛。(他家人的描述與此有些不同,他們說他沉默寡言,有時會耍點心機,另外也有提到他害羞的個性。)舉槍自盡之前,他將過去拍的家庭影片裝在袋子裡並放到車庫。他想確保那些東西不會遺失。這個舉動彷彿是對一個快樂的美國家庭致敬。如果一切都照他的計畫走,那些影片便會是倖存下來的故事,有如《可歌可泣的美國悲劇》(A Great American Tragedy)。他在手臂上寫了一個訊息。他原本不打算讓任何人看到,也沒人記得那到底是什麼。他留下了類似「我罪該萬死」的文字。
保羅說,前門上的坑洞是有一次洛基來找蜜雪兒時用力敲出來的。但是,當時他並未意識到洛基有暴力傾向,至少沒有嚴重到那種程度。那種暴力行為當下似乎難以評估,但事後回想卻清晰可辨——也就是說,家庭暴力正是如此。保羅並不是唯一一個沒能察覺凶兆的人。但試想,假如在保羅家門口又打又踹、大喊要裡面的女人出來的不是洛基,而是一個陌生人,誰不會報警?誰不會試圖插手阻止他的暴力行為?然而,當對象是我們認識的人,是其他親人,例如父親、兒子、表親或母親等,我們就不太能夠辨別暴力。保羅說,早知道他就插手,做些什麼來阻止洛基,想辦法採取法律途徑。這是蒙大拿的文化,當地民風一向自由開放,崇尚個人主義。他不信任司法體制,他覺得警方或檢察官沒有盡力拯救他的女兒。「我跟你說一件事,這會讓你更瞭解蒙大拿。」保羅說道。他跟驗屍官要蜜雪兒一家的解剖報告時,對方表示只能提供跟他有血緣關係者的資料,也就是蜜雪兒、克莉絲蒂與凱爾,不包含洛基。但是,洛基的父親戈登.莫澤(Gordon Mosure)開口要求時,驗屍官把所有人的報告都給了他。「重點是那個人怎麼看這件事。」他跟我說。這個社會是父權制度做主。保羅搖搖頭。「越想越氣。」他抽出一個棕色檔案夾,給我看他好不容易拿到的三份解剖報告。我們從凱爾的報告開始,「這個小男孩……衣服全沾滿了……血漬」。驗屍官寫下死者不久前吃了橡皮糖。克莉絲蒂的報告則寫著,身上的彈痕「多如雪片般 」,心臟重量為一百八十克。
我指著客廳裡的一塊飾牌問那是什麼。它獨自懸掛在一大片白牆上,顯得有些突兀。那是蜜雪兒的高中畢業證書。比靈斯高中(Billings Senior High School)一九九七年畢業班。那時她已和洛基同居,育有兩個不到三歲的小孩,但依然如期畢業了。她生下克莉絲蒂一年後生了凱爾。她為了「她與洛基這兩個有小孩的小孩」———保羅是這麼說的——轉到一所距離原本學校六個街區的高中。她有一台摺疊式嬰兒車,那可以容納兩個小孩,蒙大拿的冬天寒冷凜冽,而她得頂著寒風推著嬰兒車走上山。「我看過她那麼做,打從心底佩服她。」這是保羅一直害怕的時刻。他低下頭,手上正拿著那塊飾牌。剛才他站起來從牆上取下了飾牌,現在正把它抱在懷裡。他舉起手輕輕拭去飾牌上的灰塵,然後鬆開手,流下了眼淚。他深吸一口氣,試著打起精神。這正是像他這樣的為人父母不願接受採訪的原因,尤其是男性。他們會盡一切努力避免這一刻。
莎莉.賈斯塔德就不同了。幾年來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她面談。她藉由談論與盡力回想蜜雪兒的事情來延續女兒的生命。她保存了蜜雪兒與兩個孩子的所有遺物,包含信件和孩子們親手做的節日禮物、蜜雪兒年輕時寫的筆記,還有當地媒體的相關報導。她載我去看克莉絲蒂與凱爾念的學校,那裡有一顆石頭和一張長椅刻著他們的名字作為悼念。莎莉說,謀殺案發生後,她突然間老了許多,在四個月內胖了快八公斤,看起來疲憊又蒼老。她給我看蜜雪兒生前一家人拍的合照,她指了自己是哪一個,但我還是認不出她。我發現,在難以承受的悲劇面前,女性通常會滔滔不絕,而男性會沉默不語。莎莉將一連串的記憶像鳥巢般圍繞在身邊;保羅則把那些回憶像石頭一樣沉在心裡。
在莎莉眼中,蜜雪兒總流露一股超齡的責任感。她會割草皮、洗碗盤、吸地毯,全都是自己主動。有一年,她與姐姐們在「倫德的兒童天地」玩棉花糖機和其他遊戲時,蜜雪兒將她贏得的二十塊放進信封裡,裡頭還塞了一張小卡,上頭寫著這些給媽媽採買家用品。莎莉打開信封時,忍不住哭了起來。
「她〔蜜雪兒〕大可以休學。」保羅對我說。他聲音很小,聽來有點沙啞。他用手背擦去眼淚。「她讓我覺得驕傲的不是懷孕,而是繼續讀書。她沒有放棄學業。」
像蜜雪兒.孟森.莫澤這樣的女性都有著這般堅定不移的性格。她們擁有強烈的決心與毅力,想盡辦法讓自己與子女活下來。她們絕不放棄。她們之所以繼續留在虐待的婚姻關係中,是因為認清了我們多數人都不明白的事情,那是一種由內而外、看似違反常理的體認:儘管在家裡有危險,但若離開會遭受更大的危險。很多女性都有計畫,跟蜜雪兒一樣。她們留下來,等待時間過去。她們保護孩子的安全,她們努力在前線維持局勢的平衡。她們保持警覺、耐心以對,不斷尋找可以順利脫身的時機。她們竭盡所能地維持這樣的狀態…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