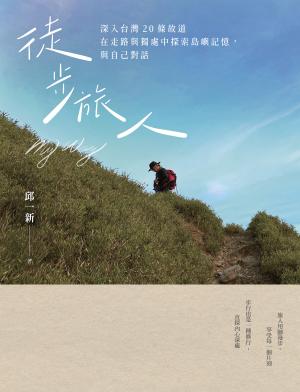緣起於遙遠的過去,卻也是此刻的片段和現象,
這往往是古老地景的雙重堅持——
放到過往中閱讀,在當下立即感受。」
——羅伯特.麥克法倫《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The Old Ways)

01 樟之細路,手作之道
苗栗頭屋、獅潭 新竹峨眉、北埔
水寨下古道:依循先民路徑的走路練習曲
「楓香樹上一顆顆的是什麼?」一抬頭,果然看到樹幹和枝枒上附著許多顆土繭擠在一起。此刻我們正在土地公廟前歇腳喝水。
「四黑目天蠶蛾的蛹。」有人隨即接答:「這種飛蛾張開羽翅時,可看到四個圈狀黑色眼紋,相當迷人;又因幼蟲愛吃楓香和樟樹葉片,也稱楓蠶或樟蠶。」
「這是風鈴木,不是洋紅風鈴木,你看它葉子掉光了,是落葉性喬木,洋紅風鈴木是常綠喬木。」
「這不是土肉桂,是外來種陰香……」有人趨前檢視葉片,做出判斷。
「你們看,這裡有三葉刺五加……」真厲害,有人在邊坡灌叢間識出這種莖脈長滿尖刺、俗稱「恰查某」的藥材。不禁聯想到五加皮酒,是否添加了此種藥用植物或同屬的五葉刺五加?
因與自然觀察作家劉克襄熟識,得以參加他策畫的「石虎輕旅行」。集聚眾人經驗一起行走,本身就是很有趣的「流動風景」,除了見證家園的美好,也走出一種過去少有人體驗的情境。
以石虎之名,自然是想在石虎棲息的淺山區走動,關心石虎棲息地和當地文史環境,也有思考走路意義的意涵,摸索島嶼旅行更多的可能性。這讓我想起一次偶然機會,二○一三年某個月黑風高夜晚,跟著「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林育秀在集集、濁水溪床以無線電追蹤野放的石虎,巡視紅外線自動相機是否有所獲,讓我在田野踏查中察覺到另一種旅行的可能性。如今,石虎,繼黑熊之後,成為台灣另一個保育「品牌」。
石虎輕旅行的成員來自各行業,原本都不認識,如何不約而同慕名參加,對我仍是個謎。猜想多半是認同劉克襄自然生態主張的讀者,在約定的時間地點一起搭車,結伴而行,途中常見知識討論,不同於一般商業性質的旅行。成員中有好幾位田野調查經驗豐富的植物專家,我尾隨在側,增長了不少知識。
是故,我所體驗的石虎輕旅行,有一個很大特色是,所有成員在徒步旅行過程中,分享動植物、歷史地理和人文知識,對未知做出智慧的推測,有時還醞釀出全新思維,說是索羅維基《群眾的智慧》在旅行領域的行動版亦可,或許能為制式旅遊團提供新的思考方向。的確,一大群人肯定會比一、兩位菁英(例如領隊嚮導)要來得聰明,不但能解決當下的問題,還能預測未知;但索羅維基也強調,要能發揮這項優勢,組成群眾的背景愈多元愈好,就像「石虎輕旅行」,或後來的「山貓小旅行」,成員背景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知識和獨立思考力,最終才能如該書名副標做到「讓整個世界成為你的智囊團」。
石虎輕旅行另一個特色是,以步行方式摸索鄉野、聚落,以及常民生活的痕跡,如拓墾年代遺留下來的義民廟、伯公廟,其間以步道、古道、田埂、圳溝、農路、鄉道、產業道路連結,似乎更契合先民日常生活的光景,因而突顯了徒步旅行的價值與信念。
此行除了健走嚮往已久的「水寨下古道」,也繞行明德水庫周邊聚落、農地、農舍。如今所謂「古道」,本是為了連結人與土地、與地方聚落而走出來的路徑,倘若不再行走,最終只有荒廢一途。
馬偕牧師在一八七二至一八七四年間,隨著探親或移墾的道卡斯族新港社(今苗栗後龍新民里一帶)族人,穿越頭屋一帶的老田寮溪(後龍溪支流),翻越鳴鳳山隘勇線,多次深入獅潭地區行醫傳教。今新店老街的劉家老宅有棵百年龍眼樹下,相傳即馬偕為村民拔牙處。
根據《教會史話》記載,在一八八四年漢人入墾之前,新港社人和獅潭賽夏族早已締約入墾,伊能嘉矩在一八九七年至新港社田調時,便曾蒐錄到一份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契約書,載明新港社人憑約備銀二百一十元、大豬二十八隻及酒儀之資給賽夏族,取得拓墾權。
漢人進入獅潭篳路藍縷大約在光緒年間,由《台灣通史》所載的「台灣貨殖家」黃南球率民丁移墾,賽夏族人只好往內山顛沛流離,獅潭遂成漢人聚落,如今散布於頭屋和獅潭之間的鳴鳳山古道群,前身有賽夏族獵徑和道卡斯族移民之路,但更多的是漢人隘勇線和伐木熬腦及運茶之路。
我們一行十多人由苗栗火車站搭公車出發,沿台13線東行,經頭屋、抵明德水庫,再由葛瑞絲香草田啟程,經上庄,穿過一號吊橋,進入水庫日新島,循產業道路與山徑繞行至水庫南岸,陡上彌勒山麓一座開山於一九四三年的普光寺。見山壁釘住三塊黃色指示牌:「RSA39 007」、「福州農場0.7km約50分鐘」、「蘧廬書院1.7km約1小時30分鐘」。第一塊牌子儼然密碼,有人解碼了,RS為「樟之細路」(Raknus Selu Trail)簡寫,Raknus是泰雅語和賽夏語的樟樹,有樟腦與產業思考的意涵;Selu是客語的小路,有深入在地常民生活的意涵;至於A39為第39段、位置編號007。走樟之細路一定會看到類似的標示牌。
目前國家級步道樟之細路總長約三百七十公里,沿台3線散布於桃園龍潭至台中東勢之間的丘陵地帶,擁有豐富多元的自然生態和人文景觀,其中數條佚失的古道經過千里步道協會手作翻修,重新找回人與土地的關係,堪稱台灣的文化路徑。
普光寺海拔不高,視野卻極佳,可及水庫,左側山壁鑲崁了十多幅詩碑,乃苗栗詩人賴江質指導寺眾之創作,字句充滿禪意,在三界火宅中取得一方寧靜。
多年前,曾載妻來明德水庫風景區尋訪一九八九年吳念真編劇的《魯冰花》電影場景。如今水庫淤積,沒有煙嵐籠罩,也無竹筏點綴,少了片中「烟波湖上蕩煙舟」那般空靈山色,滿山茶園也消失了,難以想像此地曾以明德茶(老田寮茶)聞名全台,妻只能在腦海中重播電影主題曲,我則懷想著小說家鍾肇政一九五○年代創作的時代背景——原著承襲日治以來批判社會與人性的台灣文學傳統,表面上訴求貧富差距的愛情悲劇,暗地裡卻極富技巧地藉由窮苦茶農小孩的悲劇來影射當時的政治和教育陋習。明德水庫完工於一九七○年,與原著八竿子打不著,只是作為電影場景吧。
書名的魯冰花(Lupinus),又稱「羽扇豆」,固氮能力甚高,所以,桃竹苗的茶山早年會栽種魯冰花肥沃土壤,花謝後還可充當肥料。可能因魯冰花諧音「路邊花」,帶有鄙視的貶義,小說家便藉此影射社會弱勢者吧。
因興建明德水庫故,早年沿老田寮溪走出來的田野村落和古道多遭淹沒,我臆測馬偕為了行路安全和傳福音,極可能行走水庫下有人煙的古道,再沿今「神祕谷」溪溝銜接地勢稍高的「水寨下古道」往南翻山越嶺,經今福州農莊、普光寺、蘧廬書院,接北隘勇古道、鳴鳳古道,下抵獅潭新店村地區。但公路闢建後古道便荒廢了,幸賴千里步道協會以友善環境的手作步道方式,將充滿故事與歷史記憶的水寨下古道最精采的南段(普光寺至蘧廬書院)整理出來,全長二.四公里,海拔約在一五○至四二○公尺之間。
目前山友將水寨下古道以普光寺為中繼點,分南北兩段;我曾由明德水庫南岸道路循神祕谷道路陡上福州農莊,隻身探訪北段,雜林荊棘和蛛網牽絆,底下土石鬆散,路徑不明,勉強上到支稜領略一下便折返,真是應了客家俗諺「山歌唔唱唔記得,老路唔行草生塞」。
我們由普光寺左側指月亭拾級而上,起先是石階路,接著順邊坡危崖土石路而行,山徑轉趨狹窄,林蔭濃密,藤蔓勾勾纏,爬藤粗壯,正如《馬偕日記》所載「上面有樹藤懸掛,就像船上的帆索……」,雖未趨前檢視,疑似有鴨腱藤、飛龍掌血、風藤、血藤、菊花木散布其間。
頃刻,傳來水聲,見涓涓流水從大石壁間滲出,猜想就是水寨下古道名稱由來。客語的「水寨」意為「瀑布」,但大雨滂沱才會形成水瀑吧,沿途山壁必然也是如此,成為一條「瀑布下的古道」,眼前溪溝巨石錯落,青苔溼滑,穿草鞋的先民可能就直接踏過去,草鞋雖然容易磨損,抓地力可比登山鞋強多了。為了安全故,路徑在此高繞,拉繩陡上,旋即之字形爬升,再陡下溪溝涉水而過,又緩上,此後路徑落葉堆疊,行來舒暢愜意。
突然,有位成員停下來,自顧自地說道:「當我走過自己修路的地方,便覺得很感動……」,原來她曾參與千里步道協會「馬偕奉獻之路:苗栗水寨下手作步道工作假期」。我們聽她緩緩道來,解說昔日在此維護古道的故事,例如腳踏處原本是一灘落葉爛泥巴,起初她在周遭採集搬石頭,敲碎填補路面,但經手作步道師檢視,建議在不同路況要有不同解決方案,必須順應步道所在氣候、地質和生態因地制宜,如同先民的作法,此處可將爛泥巴刮除,做出一個略傾斜的緩下坡路面,便不會積水,若要鋪碎石,也無需整片鋪,鋪一小塊墊腳石即可。其實沿途還採用好幾種繁瑣的修繕工法,如浮築路、砌石護坡、砌石階梯、橫木護坡,只是都不著痕跡,行走者沒有特別留意是不會發現的,就像一路走來看見許多船索般藤蔓在上方交織,其實是被刻意吊掛提高,藉以保護原生態景觀和行路安全,而這位女志工也透過手作之道,讓自己的生命與先民路徑有了奇妙的連結。
出口便是蘧廬書院所在的象棋坪,表示昔日此地樹杞成林,樹杞的葉子脫落後會在莖幹上留下狀似象棋的凹痕,客家人據此稱為「象棋樹」,可惜無暇搜索,會不會都被砍去做砧板和燒木炭了?在台灣行走,常遇到植物地名,約略可看出過往的人文痕跡,例如象棋林(竹東舊稱,亦稱樹杞林)、莿桐、芎林、槺榔,或我近年移居的淡水竿蓁林(五節芒很多的地方),想必都是先民對其生存環境的具體描述吧。
出口立有「鳴鳳山」、「苗22線」、「嬲崠茶亭」指標柱,後者嬲字引人遐想(嬲,漢音ㄋㄧㄠˇ,糾纏之意,此處客語音ㄌㄧㄠˋ,一群人坐著休息聊天之意),位於北隘勇古道上,但囿於時間,我們仍取苗22(南窩產業道路)而行。這自然是遵循劉克襄式「自創旅行」(自己設計旅行方式)精神,由於走的不是旅遊路線,無法預期會出現什麼樣的風景,也不知拐來拐去的道路會接到哪裡去,果然,途中便遇到收養流浪狗的住家,與主人一陣蘑菇,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一路行來,遇到的植物有大如座椅的猴板凳、呈現敗欉徵兆的開花茶樹、屍橫邊坡的菊花木、覆蓋山谷樹冠層的小花蔓澤蘭,還有土橄欖、鐵冬青、丁香,以及好幾株高大的蓪草。
眾知蓪草產業在台灣至少有兩百年歷史,英國攝影家湯姆生在其《十載遊記》便提到廈門有條巷街,家家戶戶都在摺紙花,有百合、玫瑰、杜鵑、山茶花,還說紙花材料來自福爾摩沙蓪草。其時以蓪草紙繪製的水彩畫和人造紙花在歐洲備受歡迎,可歐洲人誤以為是白米做成的紙,故稱「rice paper」(米紙),直至一八五二年才釐清由來,正式發表為新物種。
蓪草的莖髓質地近似保麗龍,常染成五顏六色作為勞作材料,五、六十歲以上的人或許都玩過吧?
但劉克襄的聯想更深邃:
「這是台灣最早被記載的植物。當年福鈞(Robert Fortune)搭船來到淡水港,上岸採集的植物便有蓪草……」
這句話引起我好奇,查閱福鈞一八五七年著作《居住在華人之間》(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有一個章節特別詳述來台始末——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日,身在福州的福鈞趁美國汽船孔夫子號為清廷載運軍餉之便,搭順風船至淡水,登岸一天,記錄下「日本百合」和蓪草,成為台灣最早的植物採集記錄者,無意間為台灣植物學揭開序幕。可惜他誤判了,前者於一八九一年被證實為「台灣百合」,後者稱為「米紙樹」(rice-paper tree)則正確無誤,可能已知蓪草在一八五二年發布新學名的事實,更清楚命名所依據的樣本與銷往歐洲的米紙畫和紙花多來自台灣蓪草,這是他渡海來台的動機嗎?
順帶一提,這位福鈞曾將中國茶樹種子和薰香茶葉的佛手柑、茉莉偷運到印度喜馬拉雅山區栽種,還連哄帶騙拐走多名製茶師和製茶設備,終結了中國對茶葉的壟斷,成為歷史上最著名的「植物獵人」。但他運用名為「華德箱」(Wardian case,英國植物學家沃德〔Nathanial B. Ward〕發明的一種密閉玻璃箱)運送植物和種子的技術,爾後也促成許多經濟作物的物種大交換,例如在茶葉之前,祕魯金雞納樹移植印度、巴西橡膠移植錫蘭,都是拜華德箱之賜。
沒多久,下到水庫,沿南岸而行,經過數戶農家曝曬大芥菜,那客家氣息令我備感親切,接近洩洪大壩時,克襄突然停下腳步:「大家有沒有聽到?小彎嘴的叫聲……」此刻劉克襄又變成昔日的「鳥人」了。這就是我覺得石虎輕旅行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在尋找奇特的景點,而是在培養自己對周遭環境與人事物的感知能力,讓看似平凡的東西顯現本質與價值。雖然克襄對島嶼的內容熟悉不過,但這份熟悉並未侷限他的視野與想像,在他的凝視下,還經常厚實了地方意涵,讓每次的石虎輕旅行走得興致盎然。對我而言,這是一種「看見」、「識見」的走路練習曲,重塑了我看待島嶼的視角…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