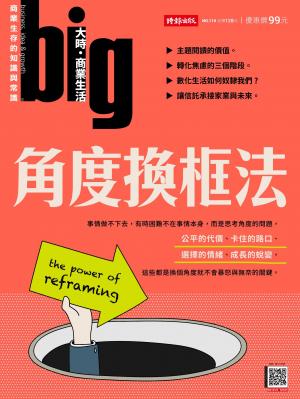事情做不下去,有時困難不在事情本身,而是思考角度的問題,公平的代價、卡住的路口、選擇的情緒、成長的蛻變,這些都是換個角度就不會暴怒與無奈的關鍵。 文/賴婷婷 ─件事可以從多個⻆度來看─目標、目的、過程、可能性、風險、價值等,每一種⻆度都是正確的切入點,只是所需的代價及其程度有所不同。從目標著手,速度很快,但有時難免會忘記當初長期追求的初衷。從風險出發,感覺很安全,卻可能因此錯失機會與可能性。注重過程,能獲得學習與沉澱,但與時間、資源之間的拉扯及平衡,需要有智慧的取捨。從價值出發,確實富有意義,但若長期下來沒有具體成果,也難以堅持。我對⻆度的理解,就像是玩拋接沙包的遊戲,每個人都希望兼顧所有面向,但我們在任何時刻終究只有兩隻手。在同一個時間點,我們所能掌握的,也就是一隻手抓一件事,一次只能同時顧好兩件事,然後依序輪替,才能接住其他不同的沙包。
OS:這一點都不公平!
感覺不公平在所難免,但我不必讓它決定我的人生 人對「公平性」的在乎,是根深蒂固的─不見得要大聲嚷嚷、表達立場,才是真正在乎平等與公平;有時候,根植於底層的「在乎」會隱晦但直接地影響自己。有一次我去買甜食,店家將甜食裝在開放式的小紙袋裡,對於當時拉著行李箱、一手拿著高鐵票的我來說,拿著這個紙袋有點不方便。輪到我前面的顧客結帳時,店員問她是否需要手提袋。我心裡鬆了一口氣:「原來有手提袋,太好了。」但輪到我時,店員卻沒有詢問我是否需要手提袋,結完帳就直接轉向下一位客人。我並沒有開口要求,因為有固然很好,沒有其實也沒關係。但我確實清楚察覺到,在那一個微秒間,心中自動浮現一絲微妙的疑惑─我很好奇店員是如何判斷一個人需不需要手提袋?在我看來,前面那位顧客的行李分量跟我差不多,也沒有特別需要空出雙手照顧小孩或長者。我是真心疑惑,為什麼店家不會詢問我需不需要手提袋?當然,這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極其微小的事,我也沒有無聊到繼續觀察店家提供紙袋的頻率。 但我衍生出一個念頭:「哪一種不公平的感覺,會讓我不願保持沉默、不願妥協,致使我真正做出行動,表達我的立場或情緒?」我從沒想過這個問題,但認真思索後,竟然也讓我對自己的底層邏輯有些新的發現。 先從原生家庭談起,我成長於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凡是家中有任何好康,自然就是直接「判定」給弟弟。這類生活事件與情境多不勝數,我卻發現自己竟然沒什麼不公平的感受。我問自己,是「奴性」使我習慣了嗎?思考後,覺得這不是原因。我認為是因為自己也很愛弟弟,所以能夠接受父母用他們知道的方式來表達對兒子的愛,而我不會因此鑽牛角尖。於是我發現,「愛」可以克服或中和我對不公平的感受。 還有一件同樣發生在生活中的小事,也讓我有類似的體悟。我還沒出嫁時,家裡只要有雞腿,全家人絕對不會去動,因為那是留給妹妹的,沒有人對這件事有任何意見。後來,當我結了婚、有了孩子後,每次買炸雞桶餐,我發現自己總是只吃雞腿,不喜歡吃雞塊或雞胸,所以我其實是愛吃雞腿的。但當我回想自己是否曾因為在家裡時老是吃不到雞腿而感覺不公平?似乎也沒有。我開始抽絲剝繭,除了因為我也很愛妹妹,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使我不會對這件事感到不公平?然後我發現,對於比我「小」的人,我似乎不會介意自己所分得的資源是否一致。這種「小」,不僅是指年齡,也延伸到我對當下情境或對方能力的主觀判斷。只要我感覺對方比較「小」,就會自動進入「讓」的模式,公平性又會被我放到比較後面的順序。
你願意為了什麼挺身而出? 剛進入職場時,我倒是頻繁地產生了「這不公平!」的感受。看到老闆老是將「很肥」的專案指派給愛徒,大家都默不作聲,我卻會大剌剌地問:「為什麼?」又或者,當老闆大筆一揮,拍板選擇了一家報價明明更高的廠商,大家都心照不宣,我卻會表態:「這不合理!」這類被視為「白目」的言行,我真的有很豐富的經驗。我也是人,當然看得見大家的驚嚇眼神,或是感受到擋人財路時的壓力。表態的次數多了,我難免被貼上一些標籤,偶爾也會被高層請去「曉以大義」,暗示我要懂得配合。 即便那時還年輕,我似乎仍隱約察覺到,若我看見自己無法理解或接受的事情,卻選擇閉嘴,那我很有可能就這麼一直安靜下去,成為那些「懂事又社會化」的同事之一,而我知道自己不想成為那樣的人。 短期來看,我那些(有時滿衝動的)表態,雖然付出了一些代價,但事實上,也使我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資訊與資源。更多時候,我因此成功得到一些原本不會知道的答案,或是不同的安排。有問就有機會,有講就有效果。我多問一句話,老闆便會多提供一些說明,讓我能理解這個決策是如何形成的;抑或是老闆沒料到會有人當面質疑他們那些昭然若揭的偏心,反而因此調整了決策或資源的配置。 我發現,很多時候,這種不公平的感受,其實源自於資訊落差。一旦採取行動來釐清後,原本那些可能會讓自己氣上好幾天、甚至錯誤評價他人的感受,就會瞬間煙消雲散。當我掌握了更多資訊後,我選擇理解公司的資源有限,這是目前最好的安排,既然如此,該做什麼就去做什麼,而情緒對我的干擾時間也會因此縮短。抑或是我實在無法接受當下的解釋與資源配置,那麼,我會選擇尊重與回應自己的感受,拍拍屁股走人。 長期來看,我逐漸成為擁有中心思想的個體,而不再是任人搓圓搓扁的應聲蟲。那些自年輕時開始累積的經驗值,使我開始有了話語權,也有機會承擔一些艱難的任務。我發現,我回應職場中「感覺不公平」的方式,是找到自己的立場,並選擇溝通,而不是悶燒。 角度換框使我比較不會被眼前的資訊所綁架。當我釐清自己長遠而言想為自己的人生創造什麼,就更能在每個當下選擇立場,並做出相應的決定與行動。當然,承擔自己所做選擇的配套後果,也是必要的代價。
SO:如果這是活出我想要的人生的代價,好吧,我願意。 OS:做好這件事有這麼難嗎?
越是不理解、不曾承擔過的人,越容易隨意評斷 我其實很排斥那些隨口說出的「輕率評論」(easy comment),說的人不痛不癢,被說的對象卻是有口難言。 看到一位年紀輕輕便位居要職的人,有人脫口而出:「他一定是有門路吧。」卻沒看見當所有人都下班後,他一個人連續好幾個月加班到深夜的背影。 聽說某個專案突然被腰斬,負責的人破口大罵:「老闆是錢太多吧,這麼浪費資源,根本不明白我們有多辛苦!」團隊不知道的是,老闆已經為資金奔波了半年、天天跑銀行,再也撐不下去。遠方的未來也許很美好,但他已擠不出半點力氣去跨越眼前的小水溝了。 走在街上,眼前出現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旁人紛紛讚揚她「真是天生麗質!」,卻不知道她已經有很多年不知道「吃飽」的滋味。 我明白那些都是直覺、直觀、輕鬆拋出的意見,不必認真深究。但這類不經思考的隨口一說,看似無傷大雅,卻可能觸及他人的痛點或敏感區域,甚至可能導致誤解或是錯誤的引導。這在個人層級上或許只是顯得輕率,但在公司層級上卻有可能引發難以處理的公關議題。 然而,最令我難以忍受的,是來自老闆的輕率評論。當老闆有意或無意地說出:「做好這件事有這麼難嗎?」我真的會瞬間火冒三丈,他難道沒看到我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一點嗎?他難道不知道我正在處理他一時興起所造成的爛攤子嗎?我真心懷疑他是不是選擇性忽略,才會對我或團隊已經忙到人仰馬翻的疲憊狀態視若無睹。 但沒想到,後來我也成了給出這種輕率評論的人。有幾次我臨危受命,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公司轉虧為盈。雖說扛著巨大壓力,但我對於雙H類型的工作(高壓High pressure、高挑戰High Challenge)是有點上癮的。 這種需要迅速解決複雜問題、要求高度責任感與判斷力的激烈環境,不僅讓我的腎上腺素飆升,也有效鍛鍊出我的心理韌性。然而,扛起P&L(損益責任)絕非易事,尤其當公司的現金已經嚴重不足時,每一分資源都得當成三倍來用。辦公室裡,各種背靠背(back to back)的連環會議不斷,一組團隊剛離開,下一組又接著進來,大家彼此打趣說:「你領號碼牌了沒?」或用意味深長的眼神看著下一組說:「輪到你了。」在兵荒馬亂的時期,只要我發現團隊未能如期、如實執行先前已經說明過的事項,就會有點惱火。有時我壓得住脾氣,有時壓不住,特別是在重要又緊急的情況下,我真的不知道耐心兩個字怎麼寫。夥伴有時試圖解釋,但又說不過我,最後便會露出委屈無奈的表情,但我看了反而更煩躁,心想我又不是沒教過、沒示範過,為什麼就不能一次做對、做好呢?「做好這件事有這麼難嗎?」「這個想法不切實際!」這些話就這樣冒出來。 回頭想想,我的底層邏輯或潛在需求可能是:「我有話就該說,大家都是大人了,這麼說沒什麼吧!」 「大家都明白我的壓力與辛苦,應該要配合我吧,畢竟我正在努力使船不沉啊!」 當下我其實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成了輕率說出評論的人;我只是想要盡快劃掉待辦清單上的項目。我的輕率評論,可能傷了人、扼殺了創意,或削弱了信任。這樣的情緒折騰使夥伴感到痛苦,我自己也不好受,但時間如洪流般嘩啦嘩啦地向前奔騰,我根本停不下來,更沒時間思考該調整些什麼(現在聽起來真像藉口)。
比無知更可惡的,是視而不見 我家附近有一間速食餐廳,當我早上七點多去坐捷運時,就會看到窗邊有一位阿嬤在寫字。起初我並沒有特別注意她在寫什麼,直到有一次當我進門買三明治,等待的時候多看了幾眼,原來她是在練習寫字,像小學生剛開始學寫字時,一筆一畫地抄寫著同一個字,整齊地寫滿一整排。阿嬤認真的神情讓我忽然覺得無比感動,那樣的畫面真美好。 對於一位素昧平生的長者,我都能抱有溫柔的情懷,那麼,對於尚未放棄公司這艘破船,還願意一起認真打拚的夥伴,我怎麼就不能多一點耐性呢?沒錯,資源不足;是的,時間緊迫;但我的語氣是可以控制的,我的方式是可以調整的。我的眼睛除了盯著那些不足、不夠好、不順利的地方,難道就看不見其他面向了嗎?於是,我開始有意識地多觀察、多提問,試著了解不同的人在執行面會遇到哪些障礙。我不再針對正在醞釀的想法潑冷水,而是好奇裡頭會不會有什麼可取的元素。 原來,我之前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後來,於公於私,對於我不了解、不確定的事,我盡量不輕描淡寫地給出評論,因為我的茶餘飯後,可能是他人數不清的徹夜難眠;我覺得稀鬆平常的議題,卻可能是他人底層真真實實的需求或痛點。我當然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妳就跟婆婆表明立場啊!免得她變本加厲,越來越誇張。」但是,需要每天跟婆婆住在一起的人不是我,擔心老公陷入兩難的也不是我,我憑什麼給出這樣的評論呢?更何況,我也無法對她搬出去住之後的人生後果負起責任,那我又有何資格貿然、毫無分寸地評論他人的處境? 成為講師後,我甚至借用了那位阿嬤練字的意象。在每場工作坊剛開始時,我會先放上「學」這個字的筆畫順序(共十七畫),邀請大家先放下心中既有的認知,以開放的心胸來看看是否有某些心態與做法可以進一步優化與調整。結尾時,我會放上「習」這個字來提醒大家,獲取知識固然重要,但也要透過反覆實踐的堆疊,才能讓所學的事物進入身體與腦袋,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學是起點,習是過程;學是知道,習是做到。想法不會改變結果,做法才會。就像學游泳,不下水練習,永遠只會是旱鴨子。 情境未變,壓力依舊,但透過角度換框,就能對情緒的轉換產生迅速且明顯的影響,甚至有許多人給我回饋:「妳怎麼能這麼有耐心?」而這真是我始料未及的轉變。
SO:卡住的地方,就是突破的破口。 OS:路是人選的,但我有得選嗎?
不是改變事實,而是選擇如何看待 我有個不知是好是壞的習慣,任何東西除以三百六十五之後,我都買得下去。一件一萬元的衣服或褲子,除以三百六十五之後變成二十七,我便會催眠自己,只要每天二十七元,我就可以擁有它,而且我值得!但事實上,我根本不可能三百六十五天都穿著它,若一個月穿一次,那成本其實是每次八百三十三元才對。但就算是一個月八百三十三元,我還是願意買,因為我值得!問題在於,我太常使用這套邏輯,因此會有很多東西不停湧入我的生活,但我卻不一定能找到同樣合理的算式來捨棄它們。 我是個念舊的人。我有一個藍色的釘書機,是我出社會後第一份工作時買的,超級好用。這些年來,我陸續買過至少二十個釘書機,卻始終沒有移情別戀,即使搬過好幾次家,這個釘書機在我的書桌抽屜裡一直都有一個位置。 我自認不是特別擅長交朋友,但我有一群小學同學、一群國中同學、一群高中同學、一群大學同學,以及每一份工作中各自留下的幾位夥伴,直到今天都保持聯繫。在社群媒體還不發達的時代,我們透過書信往來維繫感情,那些泛黃紙張上寫滿了青澀語句、為賦新詞強說愁的言語,我都留了下來。幾年前,我終於花了幾天的時間,將所有書信、便簽和卡片一一數位化,成為隨時可以調取的記憶。
閱讀完整內容本文摘錄自
角度換框法
big大時商業誌
2025/11月 第110期
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