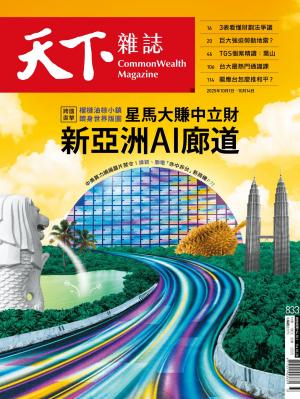星國台廠》50億美元擴廠,台星一體新模式
二十五年前,聯電蓋起新加坡第一座十二吋晶圓廠,如今不僅斬獲「非中非台」契機,年產能上看百萬片,更把新加坡廠變身車用研發基地,與台灣成雙引擎。 文—黃亦筠 攝影—莊凱程 新加坡東部的白沙晶圓科技園區,帶著幾分竹科的氛圍。園區內最醒目的建築,莫過於聯電最新的二十二奈米晶圓廠。 聯電新加坡廠資深執行廠長戴錦華,站在嶄新的廠房前,臉上帶著一絲驕傲與感慨。「終於看到半導體業又熱鬧起來,這次擴廠,等了二十年,」他說。 隨著美中科技競逐和AI浪潮興起,以及客戶對「非中非台」產能的迫切需求,新加坡再次站上全球半導體舞台的焦點。 聯電早在二○○○年就踏上新加坡,當時與英飛凌合作,興建當地第一座十二吋晶圓廠,為這座城邦的半導體產業開啟新頁。然而,此後當地鮮少有大型晶圓廠擴建計劃。 直到近兩年,隨著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去風險化」趨勢白熱化,國際大廠紛紛重返新加坡,一場空前的投資擴產潮正在這裡上演。

聯電小檔案 成立—1980年 董事長—洪嘉聰 總經理—簡山傑、王石 成績單—營收2323.03億、獲利472.11億(2024年) 主要業務—成熟製程55/40/28/22奈米為主;與英特爾在美合作開發12奈米;BCD、嵌入式高壓等特殊製程應用 全球佈局—台灣、新加坡、中國、日本
「近年地緣政治風險升高,愈來愈多企業選擇新加坡,作為分散供應鏈的關鍵據點,」聯電共同總經理簡山傑表示。 作為全球前五大晶圓代工廠,聯電在成熟製程(二十八奈米以上)具有關鍵地位,累積了五十五奈米、四十奈米、二十八奈米等世代深厚技術,並能提供物聯網、車用電子、智慧手機無線通訊等特殊製程解決方案,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隨著去風險趨勢加速,汽車電子、工業控制與消費性電子等需要穩定成熟製程的客戶,紛紛要求聯電在「非中非台」地區建置量產產線。 「需求來得很急很快啊,」戴錦華語氣興奮。 他在新加坡半導體業二十七年,二○○四年從美光來到聯電新加坡廠,一路見證聯電在這座城市從默默耕耘,到如今在星國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更目睹新加坡從晶圓代工「小配角」,在瞬息萬變的局勢中,借勢重新攀上半導體全球供應鏈上的要角。聯電這座耗資五十億美元的新廠,正是這股浪潮的領頭羊。
不只生產,更是研發引擎 過去,台灣晶圓代工廠的海外據點大多僅承接母公司技術,負責生產。然而,聯電這座新加坡新廠的定位遠不只於此。它不僅是聯電海外最重要的生產基地,更承擔「研發」與「備援」的雙重使命。 簡山傑指出,聯電已在台灣南科廠與新加坡廠之間建立了研發分工。南科主要聚焦較先進的十二與十四奈米技術及高壓製程開發,而新加坡則專注於特殊製程與車用、客製化應用的佈局。 戴錦華驕傲地說,新加坡廠「已不只是單純接台灣球,也可以發球回台灣。」他透露,當地團隊正研發一項台灣尚未具備的五十五奈米BCD製程,這是一種混合製程,對電源管理和車用晶片十分關鍵。在完成本地認證後,將反向移植回台灣,讓新加坡廠成為真正具備技術輸出能力的研發引擎。

▲聯電近年投資多放新加坡,未來重要性不言而喻。(聯電提供)
這座佔地十一.八萬平方公尺的新廠,預計明年投產。第一階段全開後,每月可生產三萬片晶圓,使聯電在新加坡的總產能突破每年一百萬片晶圓。它不僅為聯電全球供應鏈提供備援,更為客戶在地緣政治風險下,增添一個可靠的新選擇。 在戴錦華眼中,台灣與新加坡廠的關係,不僅研發分工不重疊,且聯電近年投資額大多放到新加坡。「我這邊還有空地可以放機台,支應公司後面重要的製程,」他拚勁十足地說。 台灣資源的支持,為新加坡提供後盾;而新加坡廠的在地化研發,則能為母公司注入新能量。這是雙向交流,也是文化融合。 聯電甚至在廠區設置當地罕見的綜合室內體育館,開放給新加坡在地公司、學校與社區共享,以加深文化連結並吸引人才。 戴錦華也強調,新加坡廠擁有聯電海外最大的研發團隊,將提供七百個技術職位,從新加坡本地、馬來西亞、東南亞乃至全球招攬人才,為聯電新加坡廠的長期發展儲備彈藥。 事實上,聯電與新加坡的產業連結比外界想像更深。 聯電在新加坡設立初期,測試晶圓是在新加坡本土首家半導體廠特許半導體進行的,後來特許被格羅方德收購。 新加坡半導體協會執行董事洪瑋盛回憶,過去不少工程師從特許或格羅方德轉投聯電。「這些人都是『老朋友』了,」曾任格羅方德工程師的他笑著解釋,從「DNA」來看,新加坡和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早已緊密相連。新廠落成,不僅是聯電全球 佈局的重要一步,更是台灣半導體在變局下的縮影。聯電打造出「台灣以外」的基地,為全球客戶確保供應鏈韌性與創新力。
閱讀完整內容本文摘錄自
車用晶片「非中非台」聯電推升級加坡竹科
天下雜誌
2025/10月 第833期
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