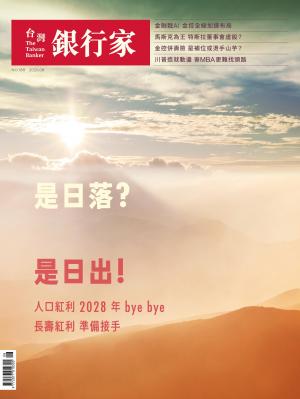少子化風暴席捲,各國雖紛紛推出催生政策,卻往往不見成效,因此,新思路是轉換視角,發展「長壽紅利」。善用健康長者的人力與財力,彌補正在消失的人口紅利,為經濟注入新動能。 董安琪 2025年,台灣面臨一連串內憂外患,除了國際上地緣政治及關稅等問題,在台灣社會,更多的挑戰正在無聲無息地發生:例如出生率低到「生不如死」、醫護人手短缺、急診室壅塞、公車缺司機、旅宿業缺工,以及勞保不斷靠撥補來延命。這些事件共同反映了一座超級冰山── 台灣人口的急遽老化。 ﹝圖1﹞列示台灣在1970、2019、2070三年的人口變化。2019年底台灣總人口2,360萬多人,史上最高,之後逐年縮減,國發會推估到2070年將不足1,500萬人,退回到1970年的人口。數字雖然相同,結構卻已然翻轉:1970年時0至14歲的小孩占總人口約4成,2019年降為12.8%,2070年將只剩6.9%;65歲以上高齡人口由2.9%先增至15.3%,再提高到46.5%;15至64歲的青壯年至2070年將降低到跟高齡人口差不多。

人口變化帶來許多挑戰。有些更迭是經濟生活的常態(如:成人尿布銷量早已超過嬰兒尿布),但也有不少衝擊造成棘手的國安、社會或健康問題(如兵源不足、生源不足、血源不足)。在此,我們聚焦於總體經濟面的三大危機:勞動不足、財政困難、醫療長照資源短缺。首先,勞動力不足不但影響國民生活的正常運行(如公車找不到司機而減班,餐廳雇不到幫手而歇業),也把總體經濟推入「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困境。其次,由於繳納稅捐與社保保費的主力是青壯年人,若青壯年變少,而領取年金的高齡者人數變多且領更久,國家財政容易失衡且加速年金破產。最後,因為高齡者人均醫療照護需求大於年輕人,人口老化下,醫療照護的人力與財力的需求不斷增加,就會出現老人沒人顧、病人沒人醫的無奈窘態。 幾個指標可以看出台灣老化嚴峻的狀況。首先是平均壽命。台灣人0歲平均餘命(簡稱平均壽命)在1981年至2023年間,從72.01歲增為80.2歲,大約每5年提高1歲,不過未來的增幅已在趨緩。第二是高齡者人口占比已增至19.5%,接近「超高齡社會」的門檻(20%)。第三是扶養比,常用的定義是工作年齡人口( 1 5 至6 4 歲) 數與非工作年齡人口(0歲至14歲及65歲以上)的比值。當這個指標小於0. 5,表示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稱為「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 d end)期。台灣的扶養比在2012年達到最低(0.347),2024年增為0.447,人口紅利期在1990年至2027年間,目前已近尾聲。 日本是當今世界人口最老的國家:平均壽命在2023年高達84.1歲,2005年步入超高齡社會,今年6月1日高齡人口占比29.4%,2004年起人口紅利已消失。相形之下,台灣還不算太老。但這個情況不久後會反轉,預計2048年時台灣高齡者占比(37.3%)將超過日本(36.8%),經濟負擔也更重(2070年台日各為1.15和0.92)。 比日本老這件事值得擔憂嗎?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機構研究,人口老化在很大程度上可解釋日本近30年的經濟不振,而且未來40年可能繼續使日本實質人均GDP下降至少12%。如果這也是台灣的未來,我們該如何應對? 在少子化方面,政府曾提出「0至6歲國家一起養」等獎勵生育政策。然而2024年的「總生育率」(一位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只有0.885,比日本更低(1.15,已是日本歷史新低)。其實,日本和韓國對抗少子化著力更深,同樣不見效果。與法國和瑞典等相對成功的例子比較,原因或許有二:日韓投入的經費遠高於台灣,可是法國和北歐更為慷慨;更關鍵的是,歐洲國家對職場與家庭內的性別平等、工作與家庭的平衡相當重視,東亞則相對不足,讓年輕人(特別是婦女)越來越不敢或不願生育子女。

人口變化帶來許多挑戰。有些更迭是經濟生活的常態(如:成人尿布銷量早已超過嬰兒尿布),但也有不少衝擊造成棘手的國安、社會或健康問題(如兵源不足、生源不足、血源不足)。在此,我們聚焦於總體經濟面的三大危機:勞動不足、財政困難、醫療長照資源短缺。首先,勞動力不足不但影響國民生活的正常運行(如公車找不到司機而減班,餐廳雇不到幫手而歇業),也把總體經濟推入「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困境。其次,由於繳納稅捐與社保保費的主力是青壯年人,若青壯年變少,而領取年金的高齡者人數變多且領更久,國家財政容易失衡且加速年金破產。最後,因為高齡者人均醫療照護需求大於年輕人,人口老化下,醫療照護的人力與財力的需求不斷增加,就會出現老人沒人顧、病人沒人醫的無奈窘態。 幾個指標可以看出台灣老化嚴峻的狀況。首先是平均壽命。台灣人0歲平均餘命(簡稱平均壽命)在1981年至2023年間,從72.01歲增為80.2歲,大約每5年提高1歲,不過未來的增幅已在趨緩。第二是高齡者人口占比已增至19.5%,接近「超高齡社會」的門檻(20%)。第三是扶養比,常用的定義是工作年齡人口( 1 5 至6 4 歲) 數與非工作年齡人口(0歲至14歲及65歲以上)的比值。當這個指標小於0. 5,表示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稱為「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 d end)期。台灣的扶養比在2012年達到最低(0.347),2024年增為0.447,人口紅利期在1990年至2027年間,目前已近尾聲。 日本是當今世界人口最老的國家:平均壽命在2023年高達84.1歲,2005年步入超高齡社會,今年6月1日高齡人口占比29.4%,2004年起人口紅利已消失。相形之下,台灣還不算太老。但這個情況不久後會反轉,預計2048年時台灣高齡者占比(37.3%)將超過日本(36.8%),經濟負擔也更重(2070年台日各為1.15和0.92)。 比日本老這件事值得擔憂嗎?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機構研究,人口老化在很大程度上可解釋日本近30年的經濟不振,而且未來40年可能繼續使日本實質人均GDP下降至少12%。如果這也是台灣的未來,我們該如何應對? 在少子化方面,政府曾提出「0至6歲國家一起養」等獎勵生育政策。然而2024年的「總生育率」(一位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只有0.885,比日本更低(1.15,已是日本歷史新低)。其實,日本和韓國對抗少子化著力更深,同樣不見效果。與法國和瑞典等相對成功的例子比較,原因或許有二:日韓投入的經費遠高於台灣,可是法國和北歐更為慷慨;更關鍵的是,歐洲國家對職場與家庭內的性別平等、工作與家庭的平衡相當重視,東亞則相對不足,讓年輕人(特別是婦女)越來越不敢或不願生育子女。
至於廣納移民,向來是許多高所得國家用來填補少子化下勞工短缺的有效工具。在台灣卻未必可行。疫情前,台灣國際移入移出的人數相當,但一直是「高出低進」(移入者主要是產業或社福移工,移出者則多具大專學歷)。近幾年,日韓積極在國際上爭取中階人力及高階人才,他們的立法比台灣快(例如日本今年已有第一位外國人以觀光巴士駕駛的身分成為「準移民」),薪資也更高,台灣未必具有競爭力。 此外,許多國家把法定退休年齡延後( 如日本立法鼓勵一般企業提高退休年齡至70歲),以促進中高齡者的就業,並舒緩年金財政的壓力。事實上,台灣中高齡者(特別是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確實不如日韓,頗有提高的空間。不過,執行不易。首先,即便台灣有《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等法條,中高齡者未必有意願出來工作,企業也很少提供就業機會。再者,延後退休年齡(或是更全面性的年金改革)的政治難度很高,2023年法國百萬人大罷工就是一例。 總之,人口老化雖然不無對策,但是對台灣而言,不是效果有限,就是實施困難,令人無法樂觀。 過去對人口老化的討論偏向負面觀點,近年來出現較正面的視角,稱作「長壽紅利」(Longevity Dividend)。這個名詞最早是2006年由美國伊利諾大學公衛學院教授Olshansky團隊提出,其含義是人類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健康狀態也持續進步,高齡者不必只是退休者、被扶養者、被照顧者,他們可以在經濟生產上更活躍,對自己更長的生命做更好的財務準備,也對全社會做更多貢獻。也就是說,人口老化是一個(隱藏的)財富,可以好好利用。 用白話來說,在2024年一位65歲的台灣人預期平均餘命是20.62年,到2070年一位65歲者平均餘命延長到25.04年。如果兩人同樣在65歲退休,且在工作期間累積同樣的財富,因為後者會活更久,總花費更多,財務不足的機率大於前者,需要倚靠家人或政府支援的機率也更高。但是,如果後者選擇多工作幾年再退休,個人財務風險和社會負擔都會改善,這就是長壽紅利。
然而,長壽紅利並不會隨著平均壽命的增加自動發生,還需要兩個條件:增加的壽命最好都是健康歲月,而且具有經濟生產力。第一個條件在台灣大致成立。根據衛福部資料,2001至2023年間平均壽命和健康餘命各提高3.48年(76.75歲增至80.23歲)和3.34年(69.11年增為72.45年),不健康餘命則在7.45年至8.47年之間波動,換言之,臥床歲月沒有明顯延長,長壽紅利確實有機會實現。 至於如何確保高齡者的經濟生產力?第一,過去談到人力資本如教育與醫療,主要對象是小孩和年輕人,但在長壽時代,也必須持續對高齡者進行投資,如加強資源在預防醫療,而非僅事後治療,並且要提供在職訓練和離職後重返職場者的技能再造,以提高高齡者的職場價值。第二,企業面對勞動者年齡結構改變,必須把許多過時的文化和習慣打掉重練,尤其需要擺脫年齡歧視、建立友善職場,並針對年長者的特性來重新設計工作內容。第三,個人要做好「活到老,工作到老」的心理準備,並且必須長期自我投資於健康與教育,還需要做好自己一生的財務規劃。第四,政府、企業、個人必須協力進行,缺一不可。 那麼,我們可以樂觀看待人口老化嗎?潛在的長壽紅利可否彌補消失中的人口紅利?哈佛大學的Kotschy與Bloom教授對2020年至2050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做估算,發現人口老化使得GDP年平均成長率從2.5%降為1.7%,但長壽紅利可以把成長率拉回到2.1%。它們清楚顯示,只要善用長壽紅利,人口老化的後果應該不如一般印象那麼悲觀。 但我們也沒有太樂觀的理由。首先,即使長壽是一項待開發的財富,我們必須先解決短期內就要爆發的問題,如勞動不足和年金危機,否則也無緣享受到長期的好處。 再者,長壽紅利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一般來說,收入高低與壽命長短有正相關,較高的收入往往意味著更好的醫療保健、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好的教育水準。如果長壽紅利排貧而不排富,似乎也不是全民之福。 潛在的長壽紅利有機會可以部分彌補消失中的人口紅利。當機會之窗打開,千萬要把握住!(作者為中研院經濟所兼任副研究員) 本文摘錄自 台灣銀行家雜誌2025/8月 第188期
閱讀完整內容
然而,長壽紅利並不會隨著平均壽命的增加自動發生,還需要兩個條件:增加的壽命最好都是健康歲月,而且具有經濟生產力。第一個條件在台灣大致成立。根據衛福部資料,2001至2023年間平均壽命和健康餘命各提高3.48年(76.75歲增至80.23歲)和3.34年(69.11年增為72.45年),不健康餘命則在7.45年至8.47年之間波動,換言之,臥床歲月沒有明顯延長,長壽紅利確實有機會實現。 至於如何確保高齡者的經濟生產力?第一,過去談到人力資本如教育與醫療,主要對象是小孩和年輕人,但在長壽時代,也必須持續對高齡者進行投資,如加強資源在預防醫療,而非僅事後治療,並且要提供在職訓練和離職後重返職場者的技能再造,以提高高齡者的職場價值。第二,企業面對勞動者年齡結構改變,必須把許多過時的文化和習慣打掉重練,尤其需要擺脫年齡歧視、建立友善職場,並針對年長者的特性來重新設計工作內容。第三,個人要做好「活到老,工作到老」的心理準備,並且必須長期自我投資於健康與教育,還需要做好自己一生的財務規劃。第四,政府、企業、個人必須協力進行,缺一不可。 那麼,我們可以樂觀看待人口老化嗎?潛在的長壽紅利可否彌補消失中的人口紅利?哈佛大學的Kotschy與Bloom教授對2020年至2050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做估算,發現人口老化使得GDP年平均成長率從2.5%降為1.7%,但長壽紅利可以把成長率拉回到2.1%。它們清楚顯示,只要善用長壽紅利,人口老化的後果應該不如一般印象那麼悲觀。 但我們也沒有太樂觀的理由。首先,即使長壽是一項待開發的財富,我們必須先解決短期內就要爆發的問題,如勞動不足和年金危機,否則也無緣享受到長期的好處。 再者,長壽紅利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一般來說,收入高低與壽命長短有正相關,較高的收入往往意味著更好的醫療保健、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好的教育水準。如果長壽紅利排貧而不排富,似乎也不是全民之福。 潛在的長壽紅利有機會可以部分彌補消失中的人口紅利。當機會之窗打開,千萬要把握住!(作者為中研院經濟所兼任副研究員) 本文摘錄自 台灣銀行家雜誌2025/8月 第1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