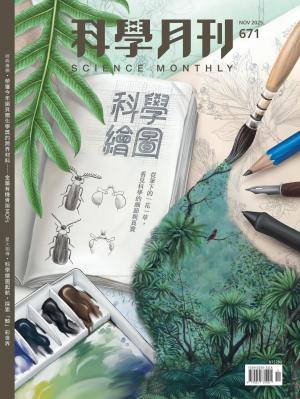王嘉琪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與地質科學系教授,研究興趣為氣候現象形成的原因及現象間的交互作用。 Take Home Message •氣候模式是一種由電腦模擬氣候系統的工具。最初的模式僅能簡單描述大氣垂直結構,隨著科學研究與電腦技術的進步,逐漸發展為能耦合各項參數等的地球系統模式。 •氣候模式可用於推估不同溫室氣體排放情境下的未來氣候變化。氣候系統本屬於混沌的系統且計算量龐大,全球科學界透過耦合模式比對計畫共享資料,作為全球氣候政策的重要依據。 •臺灣自2011年起自主研發臺灣地球系統模式,在國際評比中表現優異。未來透過持續的發展與國際合作,臺灣可更精準應對氣候變遷挑戰,為決策者提供科學依據。 讀者是否曾經感到疑惑,為什麼天氣預報只能勉強預報到一週後,氣候模式(climate models)卻可以模擬100年後的狀態呢?氣候模式提供的結果可信嗎? 氣候模式其實是一種將大氣、海洋、陸地與生物地球化學過程數學化後,以電腦程式進行模擬的研究工具,建立在大量的科學知識及電腦科技上。接下來將一同探究氣候模式的建構原理、發展歷程及應用,並說明臺灣在氣候模式發展上的重要進展與貢獻。
什麼是氣候模式? 氣候模式的建構原理是將地球表面與大氣分割為許多格點(grid cells,圖一),在每個格點上套用已知的物理及化學定律,以模擬各種氣候過程的變化,包括大氣流動、水氣蒸發、雲的形成、降水、海洋洋流與陸地植被變化等。這類模式常被稱為全球環流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GCMs)或全球氣候模式(global climate models)。 隨著科學家對地球系統理解的程度加深,以及電腦軟硬體技術與計算能力的提升,現今的氣候模式已逐漸擴充至涵蓋更多的生物與地球化學過程(biogeochemical processes),例如碳循環、氮循環等。這類模型被稱為地球系統模式(earth system models, ESMs),能模擬自然與人為過程的交互作用,提供更完整的氣候模擬能力。
氣候模式的發展 氣候模式的先驅是日裔美籍氣候學家真鍋淑郎(Syukuro Manabe),他因對氣候模式建構的重要貢獻,於2021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真鍋淑郎在他於1964年發表的論文中,使用一個僅具有垂直維度的氣候模式,將大氣垂直分層後,以簡單的能量收支概念,計算每一層大氣達到熱平衡時的溫度,成功模擬出平均氣溫隨高度變化的垂直分布,並探討平流層臭氧、二氧化碳(CO2)、大氣對流、水氣及雲對氣溫的影響。 受到真鍋淑郎的研究啟發,科學家也開始分別針對大氣、海洋、陸地與海冰等地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各自建立數學模型以模擬其變化。圖二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所發布的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中彙整的氣候模式發展歷程,以各次評估報告的時期為分界,呈現氣候模式的進展。 大氣模式首先在1970年代發展出具備三維結構的雛型,能模擬二氧化碳產生的溫室效應。而到了1980年代,大氣模式開始加入非常簡化的地表狀態(landsur face)及靜態海冰(prescribed ice)。至於最初期的海洋模式也在1980年代出現,當時僅能模擬表層混和層,還不包含洋流等動態特徵,所以被稱為「沼澤型海洋模式」(swamp ocean),並在1990年左右,也就是IPCC第一次評估報告時期,正式與大氣模式耦合在一起〔註〕。 註耦合是指不同系統間彼此影響,例如海表面溫度會影響大氣溫度,大氣溫度也會影響海冰融化,這類模式稱為「耦合模式」(coupled model)。 海洋與大氣耦合過程的發展,主要是受到聖嬰現象(El Niño)研究的推動。1987年,茲比亞克(Steve Zebiak)與凱恩(Mark Cane)兩位科學家共同發表了一篇深具影響力的論文,成功地將大氣與簡單海洋模式耦合在一起,並模擬出聖嬰現象。該模式模擬出赤道東太平洋海表面溫度上升的型態,以及聖嬰現象約3~4年的週期特徵,使科學家能在1~2年前就預測聖嬰事件的發生。這項成就大幅促進了海氣耦合模式的發展及科學界對聖嬰現象的理解。 隨後海洋模式也逐漸加入更多細節,包含表層洋流、深海環流等。到了2007年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時,大部分海氣耦合模式已包含動態海冰模式。雖然海冰的覆蓋面積不大,但由於冰的反照率高,加上海冰會阻斷海氣介面的能量交換,因此對於地球系統的能量收支有顯著的影響。 另外,科學界對氣膠(aerosol)相關的模擬始於1980年代,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研究員查特菲爾德(Robert Chatfield)與荷蘭化學家克魯岑(Paul Crutzen)〔註1〕於1984年發表了一篇開創性的論文,首次模擬來自地表的硫化物經由大氣對流傳送到高空後,透過光化學反應在對流層中、上層形成二氧化硫(SO2)的過程,進而影響雲的形成與太陽輻射的吸收。受到這篇論文的啟發,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之間,全球各地的研究團隊陸續建立出自己的大氣化學傳送模式,用來模擬硫氣膠〔註2〕在大氣中的移動與轉化。硫氣膠的化學過程後來也被納入氣候模式中,用於模擬人為排放的汙染物及火山噴發物對氣候的影響。到了第四次評估報告時,大氣化學模擬已逐漸成熟,並加入了臭氧及其他常見汙染物的相關過程。
註1:克魯岑於1995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表彰他對大氣化學的貢獻,特別是平流層臭氧的形成與分解的過程。 註2:氣膠成分相當多元,可粗略地分為含有硫成分的硫氣膠及不含硫成分的非硫氣膠。 相較之下,碳循環(carbon cycle)由於涉及了生物、海洋及地質等過程,遠比大氣過程更加複雜,因此最初期的碳循環模式為僅由兩到三個儲存庫組成的簡單盒子模式(simple box models)。一直到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的2000年代時期,隨著電腦運算能力的提升,以及科學界逐漸釐清碳元素的傳送過程,碳循環才逐步整合進氣候模式中。到了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發表時,氣候模式中也出現了可描述植被動態變化的運算模組。不過,一直到2022年的第六次評估報告,碳循環的模擬才有了較明顯的進展。但普遍來說,科學家對於碳循環的模擬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建構氣候模式需要的知識 從氣候模型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建構氣候模式或地球系統模式所需的知識相當廣泛。在科學知識上,涵蓋了物理、化學、生物、大氣、地質與海洋等領域;而在技術層面上,則需具備統計學、應用數學與數值運算的能力,並持續應用最新的電腦軟硬體。因此,發展一個地球系統模式往往需要數十人以上的團隊,由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共同合作完成。以計算空氣速度為例,科學家運用牛頓第二運動定律來描述空氣質點所受的力,這些力包括氣壓梯度力(pressure-gradient force)、科氏力、重力及摩擦力,並由合力決定加速度,再進一步以電腦程式將這組力學方程式撰寫成數值模式。當加速度計算完成後,即可推算下一時刻的空氣運動速度。而得到新的運動速度及其他物理量後,可再重新計算加速度,以不斷重複的過程模擬空氣的流動,此作法即為遞迴計算(recursive calculation)。除此之外,也應用了質量守恆、能量守恆及理想氣體方程等常見的物理定律,組成一套方程組。 目前許多氣候模式都採用同一套方程組描述空氣的流動,差別在於各研究單位所採用的「參數化」方法不同。模式的解析度取決於圖一中格點的大小:格點愈小,模擬的精確度愈高,但也需要更多的運算資源。而對於空間尺度比格點小的自然現象,例如雲的形成、對流上升、海水上下翻攪等,由於無法直接在氣候模式的網格中模擬,因此會採用一種稱為「參數化」的方法,利用簡化的公式計算小尺度現象的統計效果,並加到整體的模擬中。這種方式需要對自然現象具備深入理解,並熟悉統計方法,才能設計出合適的簡化方法,參數化處理的精確度也正是目前氣候模擬中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之一。
如何利用氣候模式推估未來的氣候變遷? 科學家在利用氣候模式進行推估時,會設定不同的氣候驅動因子,例如溫室氣體濃度、太陽輻射和土地利用變化等,模擬在各種經濟發展的情境下可能發生的氣候變化。不過,在執行層面上仍有許多需仰賴全球合作的技術細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氣候模式的運作需要長時間積分,模擬長達百年以上的結果,運算資源需求極高。再加上氣候模式的開發與維護需仰賴大量人力投入,一個研究單位通常難以同時負擔兩套以上的完整氣候模式。 但由於氣候系統本質上是高度非線性的混沌系統,即使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經過一段積分時間後仍會出現差異。因此,科學家需要在相同條件下進行多個不同氣候模式的模擬,再透過統計方法彙整大量模擬結果,求得平均值及最有可能發生的氣候變化範圍。 為了產製大量相同條件下的模擬結果,全球氣候科學界自1995年起合作推動「耦合模式比對計畫」(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CMIP),目前已邁入第六期。該計畫由國際團隊共同擬定各種暖化情境,包括未來可能的溫室氣體濃度變化、氣膠排放量與土地利用變化等,並統一提供給參與單位進行模擬。模擬產出的資料會依統一格式整理,透過全球共享資料庫交換與應用,自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以來,氣候推估的研究便大量採用來自CMIP的模擬結果。
臺灣的地球系統模式 為了培養本土氣候研究人才並積極參與國際氣候科學社群,臺灣自2011年起展開了「臺灣地球系統模式」(Taiwan Earth System Model,TaiESM)的自主研發計畫,由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導。Tai ESM已成功參與CMIP第六期,其整體模擬表現在國際評比中優於CMIP第六期模式的平均水準,展現出臺灣在國際氣候科學領域的實力與貢獻,也是本土氣候研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氣候模式結合了多個科學領域的知識與大量的運算資源,是目前人類研究氣候系統行為最可靠的工具。隨著模式技術的進步與全球合作的深化,科學家能更深入地探索氣候系統中各種交互作用,並評估人類活動對未來氣候可能造成的影響。Tai ESM參與國際耦合模式比對計畫,展現出本土科技發展與全球連結的實際成果。透過不斷累積的資料與技術,臺灣將能更穩健地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也讓決策者與社會大眾能有更多科學依據可循。
延伸閱讀 1. Chatfield, R. B. & Crutzen P. J. (1984). Sulfur dioxide in remote oceanic air:Cloud transport of reactive precursor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Atmospheres, 89(5), 7111-7132. . Manabe, S. & Strickler, R. F. (1964). Thermal Equilibrium of the Atmosphere with a Convective Adjustment,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21(4), 361-385. 3. Zebiak, S. E. & Cane, M. A. (1987). A Model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Monthly Weather Review, 115, 2262-2278. 閱讀完整內容本文摘錄自
我們能預測百年後的氣候嗎?揭開氣候模式的祕密
科學月刊
2025/11月 第671期
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