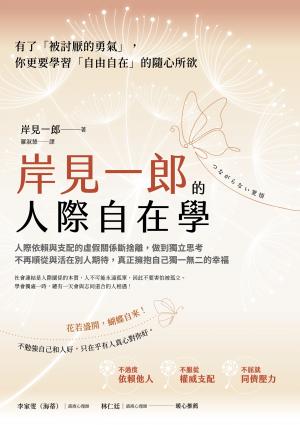守望相助的「社會情懷」
人無法獨自一個人生存。就算一個人獨居,也不可能在不受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存活。
所謂與人建立關係,並不意味著與某人在一起。有時就算身邊沒有半個人,還是能夠感受到自己與某人的連結,相對地,有時就算和某人處在同一個空間,還是可能感受不到自己與對方之間的連結。
德語有個單字「Mitmensch」。複數形是「Mitmenschen」。「mit」的意思是「與」,「menschen」則是指「人」,因此「Mitmenschen」的意思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這個單字的反義詞是「Gegenmensch」(複數「Gegenmenschen」),意指與人「對立、敵對」(gegen)。只要仔細比對這兩個單字就能知道,「Mitmenschen」並不光只有連結的意思,同時還含有「接近、親密」的意思。因此,我都是把「Mitmenschen」翻譯成「夥伴」,「Gegenmenschen」翻譯成「敵人」。
「社會情懷」是阿德勒個體心理學的關鍵概念。這個名詞是從德文「Gemeinschaftsgefühl」直譯而來的,除此之外,由前面所提到的「Mitmenschen」所衍生而出的「Mitmenschlichkeit」也是被用來表達社會情懷的名詞,意思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只要與人建立關係,對方就能夠在你有需要的時候,成為幫助你的夥伴,阿德勒認為這才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的相處方式。不過,這並不僅僅意味著一個人為了生存,就需要別人的幫助。
在其著作《尋求真正的生活方式》(暫譯),神學家八木誠一使用「Front」(面)這個名詞來說明人我之間的關係。八木將人應有的生活方式描繪成四邊形,並且四邊的其中一個邊呈現的是虛線,而不是實線。這條虛線是為他人所敞開的,便是人與他人連結的地方。換言之,「自己」之中沒有他人,是沒辦法生活的。

為了填補缺失「虛線」
人是以「面」來與他人連結的。為他人敞開的邊是虛線,而不是實線,所以必須和他人銜接才能夠形成完整的「面」。填補「我」的虛線,不僅能夠讓自己存活,同時也可以讓其他人存活。
就如前面所說,人的本身並不完整,無法獨自圓滿,必須靠他人來填補缺漏的那一邊,就這個意義來說,便是與他人連結。
這個連結不僅限於活著的人。當身邊有人過世的時候(尤其是失去家人或至親),總會有股強烈的失落感襲上心頭。悲傷之所以遲遲無法消散,就是因為填補虛線的那個人不在了,並且他曾填補過的這條邊沒有其他人能夠替代。
有些人並不會這麼看待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連結,而是直接把他人視為「敵人」。其實應該不是一開始就是如此吧?或許是因為過去曾經有過不好的經驗?曾經以為對方應該是能夠幫助自己的「夥伴」,卻在某天成了企圖傷害、陷害自己的「敵人」。但阿德勒認為人和人之間不應該是敵對,而是相互連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阿德勒在擔任軍醫的時候提出了這個社會情懷的想法。在戰場上,人們互相廝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這樣的情況下,將士們的心不可能不生病。於是阿德勒便開始投入戰鬥壓力反應(Combat Stress Reaction,CSR)的治療。
阿德勒曾經親眼目睹人們在戰場上互相廝殺的慘狀。儘管如此,他依然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要相互連結,而不是敵對。
在服兵役的休假期間,阿德勒在維也納的中央咖啡廳,首次把社會情懷的想法分享給朋友。「Mitmenschen」的意思幾乎和「鄰居」(Nächster,Nebenmenschen)相同,所以阿德勒的社會情懷和耶穌所宣揚的「愛鄰舍、愛仇敵」的理念十分相近。結果,突然聽到這些「宛如傳教士般的言論」(博托姆《阿德勒傳》,暫譯),朋友便因為無法認同「宗教性科學」(前述書籍)而離開了阿德勒。
和阿德勒同樣有過戰爭經歷的佛洛伊德提倡「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他認為這種自我毀滅的衝動本能,會在對外的時候產生攻擊性。
針對這個攻擊性,佛洛伊德說明「人類天生就有攻擊他人的傾向」(《文明及其不滿》)。他表示愛仇敵的命令就等於是在「強烈抗拒人類的攻擊性」(前述書籍),「愛你的鄰居如同鄰居愛自己一般」,這句話是無庸置疑的;但是陌生人不僅不值得愛,反而還可能引起敵意,甚至仇恨。佛洛伊德認為愛鄰舍是「理想命令」,是違背人性的(前述書籍)。
難道像耶穌或阿德勒那樣把他人視為鄰舍、夥伴,就是「違反人性」嗎?
基因中對殺戮的抗拒
戰場上的士兵們之所以心理生病,並不光只是因為害怕自己被殺,也是因為他們總是猶豫是否要將槍口對準敵國的士兵。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戰場上與敵人對峙的士兵,處於若不先開槍射擊,就一定會被敵人射殺的境地。然而,真正扣下板機的人並不多。因為在與敵人對峙的瞬間,他們會變成「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戴夫.葛司曼《戰爭中的殺人心理學》)。
但這樣就無法與敵人作戰,因此之後的戰爭便引進了反射訓練遊戲,果然帶來顯著的效果。當士兵們與敵人對峙時,他們會在腦海浮現出敵人中彈痛苦掙扎的畫面之前,反射性地扣下板機,如此一來就不會再受到良心的折磨。
不同於地面作戰的情況,士兵從飛機上面投擲炸彈或是發射飛彈的時候,腦海浮現的不是地面作戰時的敵人,而是自己正在殺人的猙獰面孔。透過訓練,士兵就可以反射性且下意識地投擲炸彈或是發射飛彈。然而,自己殺人時的猙獰面孔、敵人死亡的模樣,還是會在腦海中回放。因此戰爭結束之後,仍然有許多人承受著漫長的心理折磨。
對於伊拉克戰爭,池澤夏樹是這麼說的:「以美國的觀點來說,導彈擊中的是建築物3347HG或是橋梁4490BB,這類抽象的符號,而不是名為米莉安的年輕母親。可是,死去的人是她。是米莉安和她的三個孩子、她的堂弟年輕士兵約瑟夫,還有她的父親農夫阿巴杜。」(《跨過伊拉克的小橋》,暫譯)
如果要發射導彈,就不可以看臉。不要把它視為奪走人命的舉動,而應該把此舉看成破壞物品。如果做不到這個地步,人和人就無法敵對。由此可證,人和人之間並不該是敵對的,相互連結才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相處方式。
呼救其實代表著信任
前面以戰場為例,說明了連結本來就是人類相處應有的方式,但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明顯可證的事例。
例如,在電車上尋求幫助的情況。只要有人需要幫助,不管那個人是誰,總會有人出面提供協助。和辻哲郎是這麼說的:
「人之所以向他人尋求幫助,是因為打從一開始就相信他人是自己的救世主。」(《倫理學》,暫譯)
有些人就算遇到尋求幫助的人,仍不願意提供協助。某些人的確對他人漠不關心,但大部分的人還是會想提供一臂之力。然而,也確實有些人心有餘而力不足。
在明白這一點的前提下,尋求幫助的人依然相信他人會成為那個伸出援手的人,而向對方尋求幫助。換句話說,呼救的聲音其實就是種信任的聲音。
這種信任只會在生命瀕臨危急存亡的特殊情況才會出現。當你迷路的時候,只要附近有人經過,即使對方是個陌生人,你依然會開口問路吧?
「就算完全不知道那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有著什麼樣的心態,仍然會深信眼前的這個人不會欺騙自己,能夠帶領自己走出迷惘。」(前述書籍)
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時候,在巴黎夏爾.戴高樂機場碰到路人問我前往市區的方法。所幸我能夠憑藉著出發前做的功課回答對方,如果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回答的話,或許提供的資訊就會是錯誤的。向我問路的人深信,只要找人問,就一定能夠得到答案。
或許有些人被問路的時候,會很壞心地刻意說謊。「然而,那只不過是對方缺乏預期中的親切態度罷了,並不能推翻掉問路人的那份信任。」(前述書籍)
撇除某些例外的情況。大部分的人在問路的時候,還是會相信對方會為自己指引正確的道路。基本上,如果對方不知道路,就會直接回答不知道,應該沒有人會故意報錯路,雖然我不敢百分之百斷言,不過,我想應該沒有那樣的人吧!
就算問路人真的被騙了,日後再次迷路的時候,應該還是不會放棄問路。你會覺得應該只是報路的人搞錯了而已,不是存心要說謊騙人。
這種信任是非常普遍的,沒什麼特別。搭電車的時候,你不會認為同車的人可能對乘客造成危害。如果你會那麼想,就不可能搭電車。
不過,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向其他乘客攀談。有人看書、有人看著窗外。在乘客爆滿的電車中,人與人的距離十分靠近。有時你甚至必須對旁邊的人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來避免人擠人帶來的尷尬感。
可是萬一發生了緊急情況,大家還是會互相幫助。那個時候,即使互不相識,仍然可以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強烈連結。
或許就算尋求幫助,也沒有人會伸出援手。或許開口提問,仍可能遭到無視。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在開口詢問的時候,信任足以填補那個未知。如果認為他人可能是企圖趁隙陷害自己的敵人,而無法信任對方的話,就很難在世上生存下去。
人之所以向尋求幫助的人伸出援手,是因為知道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哪天也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
為何會冷漠旁觀?
不過,有些人並不那麼認為。阿德勒舉了這樣的例子。
某個年輕男子和好幾個朋友一起去海邊遊玩。當時,其中一個人在碼頭旁邊,因為失去平衡而跌入海中。那個年輕人探出頭,好奇地看著朋友沉入海裡。事後大家才發現,當時他除了好奇之外,內心別無其他波瀾。
「雖然這名年輕人這輩子從沒有對任何人做過什麼虧心事,甚至與他人也都相處得十分融洽,不過他的社會情懷卻十分淡薄,這一點是騙不了人的。」(《性格心理學》,暫譯)
阿德勒之所以說年輕男子的「社會情懷十分淡薄」,是因為朋友的恐懼明明無比鮮明,他卻能夠若無其事不採取任何行動,這代表這名年輕男子和朋友之間沒有半點連結。就如前面所提到的,代表社會情懷的「Mitmenschlichkeit」,意思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為什麼說這名年輕男子和朋友之間沒有連結呢?因為他只關心自己,並不認為發生在朋友身上的事情和自己有任何干係。
看到朋友落海的時候,他完全沒有想要馬上跳進海裡救人的意思。一般來說,當朋友發生意外時,正常人都會試圖出手相救。只是一味觀望彷彿事不關己的行為,實在非比尋常。
阿德勒的社會情懷,在英文裡譯作「social interest」,意思是「社會興趣」。如果和對自己的興趣(self interest,有「自利」之意)相比,社會興趣也可說是「對他人的興趣」。阿德勒表示,「對自己的執著」(Ichgebundenheit)就是個體心理學的核心議題(《阿德勒個體心理學》),意思就是把一切事物與自己連結、串聯(Binden)在一起。
對朋友感受到的恐懼不甚在意、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對他人沒有絲毫興趣,因此平常就對與他人連結沒什麼感覺。像這種不與他人連結、對他人完全不感興趣的情況,並不是正常該有的行為,這其實從人們在電車上對求助者伸出援手的反應,就能清楚了解。不過,雖然有人會在非常時刻試著給予協助,但在日常生活中仍有許多人只關心自己。正因為如此,阿德勒才會把「對自己的執著」視為問題。明明與人連結是人應有的行為,為什麼只關心自己的人卻仍有那麼多?< 閱讀完整內容